關(guān)于因為那年去了那兒的作文
那一年,我們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輕人相聚一起,來到陜南的一個小鎮(zhèn),開展所謂的社會實踐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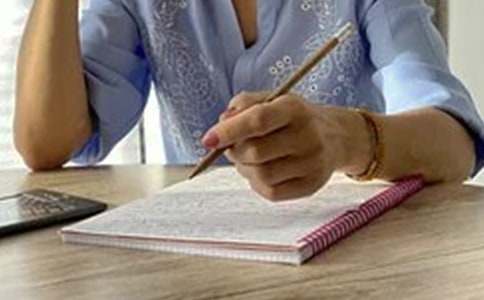
終因“天命”難違,我與小劉、小李一道被分配到環(huán)境最為艱苦的一個村上去工作。
三月初的一天,我們?nèi)瞬惶樵傅叵嗉s到村上去落實年度扶貧計劃,背叛午飯,一路小跑著去趕船,等了二十多分鐘,船公才慢條斯理地掉轉(zhuǎn)船頭,搖響柴油機徐徐前往,我們拾得一條長凳,并肩靠坐在船頭上,任憑細風吹打著面頰,更無心觀賞陽光下微波逐浪而折射出的縷縷斑斕。
約模個把鐘頭之后,我們下船行走在進村的羊腸小路上,翹首仰視,偌大的一個天一下子變成了一條縫兒,兩邊的山也仿佛在慢慢靠攏,欲將夾腹其中的趕路人擠碎似的。這里沒有公路,更不用說電話了。唯一的景致當屬農(nóng)業(yè)學大寨時期留下的一道水渠,但里面充滿了亂石,生長著野草。駐足山腰,環(huán)顧四野,一些迎春的枝條卻懶得發(fā)芽,只有遠處三兩枝野桃,盛開著耀眼的鮮花,才讓人感覺到一點點春的氣息。
當晚,我們投宿在老支書家。晚飯后,我們圍坐在小小的火爐旁,傾聽老支書講述這里的村況,老支書是一位六十有余的慈祥長者,已于前年卸任,但還兼任著這里的支部委員和村醫(yī),說話間就不時有村民前來問詢治療一些疾病的“土單方兒”。這是一個百十來戶的小村莊,其實是稱不上村莊的,五百多口人散居在十來個山峰澗嶺間,幾乎沒有水田,只有人均六七畝的貧瘠的“薄殼兒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成為這里村民生存的時間表。
村上有一所不完全小學,只有四個年級,二十多個娃,早上九點上課,下午三點就放學了,是因山路崎嶇,路途遙遠,為娃們的安全考慮。村里沒有其他副業(yè),只有少量的蠶桑和茶葉,再就是每戶年養(yǎng)一兩頭生豬而已,地里的莊稼就全靠老天照應(yīng)了,災(zāi)害幾乎是每年都有的。老支書算是村里的“上等”人家,家里的電器最好的也只是一臺14吋的黑色電視機,但信號極差,多因無法收看而成擺設(shè)。晚間洗漱時,望著只蓋住盆底的洗臉水,方知這里非常缺水,最遠的人家一天僅能擔回四五挑水。
是夜,聽得同床歇息的小劉感嘆這里生活的艱苦,環(huán)境的落后,我心中也產(chǎn)生了一種莫名的傷感,輾轉(zhuǎn)反側(cè),思緒萬端,竟一夜沒睡安穩(wěn)。別的、精神什么的更提不起來了,自然環(huán)境的惡劣,生活條件的艱苦是我始料不及的,難怪這里的村干部也如走馬燈似的頻繁的更換著。說是要做點兒事情,但農(nóng)家多年的積蓄也在前些年每戶幾百元的集資拉電給花銷了。
這不,同行的小劉、小李也尋找借口鬧著要回去。當他們再次借故要盡快回去時,我這個小組長卻不得不猶如這里的主人,挽留他們再多呆幾日。就這樣,一恍又過了三天,我們協(xié)同村組召開了群眾會,走訪了二十來戶農(nóng)家,了解到了不少情況,我的筆記本上也密密麻麻地寫滿了三十幾張,這發(fā)自肺腑的一句句平實動感的熾言,和幾天來熱情款待的一杯杯自釀的包谷酒,一碗碗特意調(diào)配的.兩摻面,蘊含著這里的鄉(xiāng)親對我們多么大的期盼啊!
當我們要離開這個村的前一天,我們從山頂滑落一條小溪,去向支書和村長道別,遠處不時傳來一聲聲清晰厚重、節(jié)奏和韻的“咚咚咚”的響聲,回蕩在這壅荒的山野里,格外悅耳,同行的一位村民指著小溪旁一座石板蓋頂?shù)男∥菡f:“那就是造紙坊”。“造紙?”我的腦子立即閃現(xiàn)出兩個鏡頭:一個是教科書上介紹的1800多年前東漢時期我國發(fā)明的造紙術(shù),一個是幾年前在南方學習時曾見到過的現(xiàn)代化的造紙廠,在這窮村僻壤,竟也有這樣的稀奇事兒?
想著想著已走進了小木屋。這是一幅怎樣的景觀呀,那發(fā)自聲響的居然是一個直徑約尺余、高約兩尺的木墩,一端套著一丈多長的方木柄,木柄中央立一木支架,另一端的木撬下則用腳有節(jié)律的踩踏,用于去搗碎放在一塊麻果石上的構(gòu)樹皮!待將樹皮搗成泥狀時就倒入一池子里,那化漿池是用石塊兒砌成的長方形,約3個平米,一師傅正用一被稱為“簾”的竹具在池子里撈“紙”,然后一簾簾的排放在室內(nèi),涼干了就成了紙。頭質(zhì)的當?shù)囟冀凶髌ぜ垼米髂旯?jié)糊燈籠、貼窗戶、做鞋樣兒等,都有著天然廣泛的用途。
我們很好奇的輪流“露了一手”,自然是令人啼笑皆非。些時,再次環(huán)顧全屋,那簡直是木與石的世界!我頓然感悟到,這里的村民正是用勤勞智慧的雙手,巧妙的把木與石結(jié)合在一起,那每一聲響,就是對世人的召喚,那每一簾紙漿,盛滿的都是希望與夢想。
翌日清晨,我們離村而返,肩上依然沉重,可卻是一種充實感,我們一路回味著初到這里的一個個大大小小的故事,暢談著應(yīng)盡心盡力為這里的鄉(xiāng)親辦點兒實事。不覺間,支書家的那只小花狗,也不知何時掙脫了韁繩,拖著長長的鐵鏈,一直送我們來到河邊,默默地注視著我們上船,離去。
這次經(jīng)歷雖已過多年,但當時的景況會時不時地在腦際泛起,在那一年時間的社會實踐里,雖然我們盡其所能,為這個村翻修梯田,興修水利,發(fā)展林果,建修校園等等,但成果終究是有限的,也不知現(xiàn)在那里的村況怎么樣了。我在想,無論如何,我還是要發(fā)起邀約當年的小年輕定要回去再好好走一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