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那村那景那事散文
下午坐在辦公室閑來無事,看了莫言寫得幾篇關于兒時記憶中山東老家的散文,就像多年前看《平凡的世界》一樣,勾起了我對自已家鄉的記憶。也許是所生長的時代不同的緣故吧,雖然我的家鄉現在依然不富裕,但莫言作品中家鄉的畫面要比我的家鄉“清瘦”的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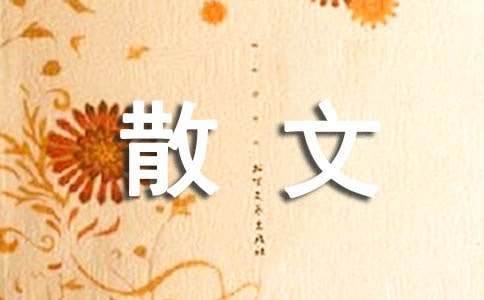
我的家鄉座落在一個山頭上,海拔很高。這就注定了我們出行不是“下山”就是“爬山”,同時也注定了我們沒有溝澗,沒有山泉,只能靠旱井收集天上的雨水來飲用。以至于后來上初中去鄉政府所在地的村里住校時,同學們都會打趣地稱我們村的同學為:“干山圪梁上的”。雖然生在山頭上會遭用水難的罪,但我覺得山頭上也有它獨特的魅力。它空曠、高遠,有一種目極千里之外且居高臨下的感覺。每當風起云涌時,我們可以看到天際四周不同的云圖,這就使得村里的小孩都有判斷哪邊將要下雨、哪邊正在下雨、雨下得大小的本領。過年時,走到我家屋外的空地上便可望到東北角上縣城的彩燈猶如一條火龍,眨巴著眼睛,熠熠生輝……
我家位于村東頭。雖然現在全家人都不在村里住,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修砌得新窯洞也已“鐵將軍”把門,但我的記憶中更多的還是那個朝東的舊院子。土坯圍墻,磚頭框架的木頭大門,它總會走進我的夢里。老屋的院子里有石磨,有石床,石磨和石床是夏天午后我們兄弟姐妹五個做作業的好地方。那時的課外書不多,也就是一些小人書,還有當老師的.父親從學校借回來的作文書、學習報、演講與口才等。坐在石磨上美滋滋地看書的情景至今依然記憶猶新!
村里的山坡、田間地頭是我們玩耍和勞作的大舞臺。那時的家長對孩子都是開放式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稱做“放養”。孩子們沒有現在的孩子“寶貝”,四五歲大時就三五成群地在陡峭的山坡上瘋跑,采野花,摘野果,有的還拔一袋一袋的草喂家里的牲畜,也有的挖板蘭根、拾桃核杏核晾干賣錢。春天雨后,大人在地里刨坑,小孩子們跟著一顆一顆地往地里埋種子。大一點的孩子拿鐵鍬、镢頭翻地。等莊稼長出地面,還要鋤三四遍草方可作罷。由于陰天鋤掉的草很容易再把根栽到地里復活,所以鋤草時必須是晴天太陽艷時。我最怕曬太陽了,也不愛干體力活,所以總能避重就輕。哥姐們上地,我有時就選擇在家給他們做飯送飯。拾棗、掐谷穗、掰玉米棒子、摘豆角、給棉花下心條掐枝杈上長出的斜條,這都是我的強項,也不怎么累、干活時也能任由思緒飛舞,只管機械性地動手便行。
兒時的娛樂項目大部分都是“純天然”的。跳繩、踢毽子、跳方格、踢石片、彈杏核、滾鐵環等。由于我們兄妹們一慣很“文”,所以這些項目我們都比不過同齡人。一九八三年,村里有了第一臺公共電視機,我們傍晚從地里回來就去那里看電視。由于長得矮,站在人群里看不見,所以大人們總把我們抱到打場機或木椽堆上。《霍元甲》、《陳真》、《十三妹》就是我看到的最早的電視劇。后來,同村的舅舅家有了電視機,我們兄妹總相跟著去看。我們兄妹小時候戲稱舅舅家為“花果山”。舅舅家種著桃樹、杏樹、李子樹、小果子樹、大果子樹、梨樹、蘋果樹等,所以看電視之余總能大飽口福,這也成為我們童年快樂記憶中的一部分。隨著在電視中看晚會,聽電視劇的插曲,我愛上了聽歌、唱歌。由于家中沒有錄音機,就經常跑去當時爸爸當小學校長的同學家中去聽。抄歌詞、學唱歌也成了那時的一大樂趣。
兒時上學,沒有現在的孩子有壓力。大人們沒有太大的要求,周邊村里的家長們更不重視,農忙時甚至還要孩子們充當勞力,老師也沒有城里的老師們下功夫,所以學業總是能在輕輕松松中完成,筷子里拔出的那根“棋桿”便是日后能考上中專、師范、大學等院校的。對于上學最大的記憶就是上初中住校時吃窩頭、稠和子飯那段餓肚子的記憶。每天兩頓飯,早飯是稀飯窩窩頭,下午的飯是一個饅頭和在稠小米飯中煮著面條的和子飯。由于用于做飯的小米、白面、玉米面,都是每個學生每隔兩星期按學校通知的斤數從家里帶的,所以質量不一,經常會在飯里吃到小蟲子。也正是這段困苦的經歷,使我對現在衣食無憂的生活心存感激!
在時光的流逝中,兒時的記憶已漸行漸遠,但那段猶如橄欖般苦澀而又甘甜的歲月像一幅“豐滿”的油畫把我童年以及少年時的生活妝點的多姿多彩!
【那年那月那村那景那事散文】相關文章:
那年那月那村散文05-23
那年.那月.那落花散文05-26
那年那月那星辰散文01-08
那年那月那生活散文12-31
那年那月那心事散文03-25
那年,那月,那花開04-22
那人·那事·那景10-02
那人·那事·那景10-02
那年那月散文0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