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院的蛙鳴的散文
那天夜里,當咕咕呱呱的聲音傳入我的耳鼓,使我放下《我與地壇》的時候,我并不知道確切的時間。我是看了表之后才發現,已經凌晨一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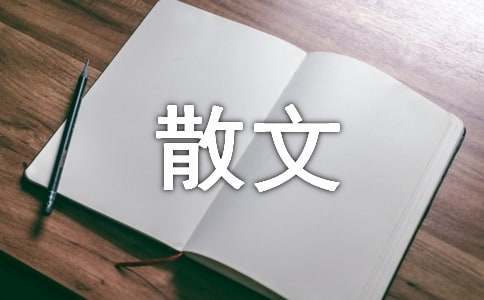
我關了臺燈,起身來到窗前,將額頭抵在窗戶玻璃上往下看。皎潔的月光被微風吹散成無數碎片,在那高低不一的樹叢上面反射著葉子的舞姿,窸窸窣窣,閃閃爍爍,與咕咕呱呱的蛙鳴配合得那樣和諧。
我住在6樓,這是魯院大樓的最高層。樓前那片并不算大的園子被我一覽無余。我驚奇地發現,左側那個水泥池子里已經有水了。而在此之前,那個池子里干凈得可以攤曬面粉。每天傍晚,我還到那下邊去走走。現在卻突然就明晃晃的一片,突然就有了蛙的鳴唱,怎不叫人喜出望外呢!
我已經很久沒聽到蛙鳴了。
讀小學的時候,校園的前面和東面各有一個池塘,我們在教室里抑揚頓挫地朗讀課文,池塘里的蛙就此起彼伏地咕呱鳴唱。
讀中學的時候,學校的西側也有一個池塘,但是那個時候我們卻很少朗讀了。而蛙鳴卻始終伴隨著我的思緒,像歡快的音符一樣在那些文字和數學公式間跳躍。
后來,我到了四季如春的云南邊疆當兵,我們的營房背后是一條綠草如茵的山谷,谷底有一條小溪,溪水清澈見底。學習訓練之余,我常約上幾個戰友到小溪邊上,或看書,或聊天,抑或是如數家珍一樣炫耀著各自家鄉的好處。
那時,我已經走上了業余文學創作的道路。每當夜深人靜,我伏案寫作,山谷那邊就非常清晰地傳來清脆的蛙鳴,而我的文思也像溪水一樣涓涓不斷,我一度懷疑那些創作的靈感就是蛙聲喚來的。1997年秋,我寫了一篇跟蛙有關的散文,發表在《文山日報》上,其中有段文字是這樣寫的:“我開了門走出屋,沿著營房背后的小溪邊走邊看,小溪俏皮地打個滾,匆匆趕約去了。幾只青蛙蹲在卵石上引頸高歌,好像在舉行月光晚會似的。我無意打擾它們,可它們已經發現了我,全都打住歌喉,爭先恐后地往水里跳,把月亮都撞碎了,就像撒了一把銀燦燦的花瓣在水面上。這些花瓣打幾個漂,蕩幾圈漣漪,便又簇擁著堆到了一起,月亮也恢復了橄欖球的樣子。”這篇散文受到戰友們的好評。
2004年,我從部隊轉業回到高密以后,好像再也沒聽到蛙鳴了。距離我家兩公里范圍內沒有灣塘,我供職的單位周圍也沒有蛙的棲息之地。上下班都在那條喧鬧的主街道上往返,我的生活幾乎被固定在家和單位這兩點一線上了。現在回想起來,這些年我很少寫甚至常常抓耳撓腮也寫不出東西來,一定跟失去了蛙鳴的陪伴有關。
正當彷徨無奈之際,卻突然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我被魯院錄取為第二十屆高研班學員。對我來說,這是一個意義非同尋常的重大事件。回顧我40多年的人生歷程,曾遇到過許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或驚喜,或憤怒,或收獲,或挫折,因為突如其來,所以記憶深刻。我萬萬沒有想到,到了人生過半的年紀,竟然又能上學讀書。我想,如果我的肉體生命可以以此為界點分割成兩半的話,那么這件事對我的精神生命同樣是一次對半分割。
來魯院之前,我曾謀劃著如何利用這兩個月的機會,把北京城好好地逛一逛。雖然我不是第一次來北京,但以往都是匆匆路過,北京的景點除天安門外都未去過。我對妻兒說了我的計劃。先去長城,因為一直受到“不到長城非好漢”說法的影響,我要去體驗一下當“好漢”的感覺。然后再去故宮、頤和園、奧運村、圓明園遺址,還有清華和北大的校園。如果還有時間的話,我還想坐上人力車去逛一逛北京的老胡同。
然而來到魯院后,這些想法竟蕩然無存了。我哪兒也不想去,就想在魯院安靜地待著。除了參加學院組織的'集體活動,或找同學交流一下心得,我喜歡在宿舍里看看書,整理學習筆記,或者到教學樓前的花園里走一走,欣賞一會兒芍藥的嬌艷,摸一摸毛茸茸的青杏,摘幾顆熟透的桑椹放在嘴里慢慢品咂。更多的則是在寧靜的月夜,獨自到魯迅、茅盾、老舍、朱自清等人的塑像前的連板椅上安靜地坐著,聽著樹葉的碎響,看著斑駁的月光,與大師們進行穿越時空的對話。這是我最為幸福的時光。
更讓我欣慰的是,來了不到10天,突然又聽到久違的蛙鳴,一下子喚醒了沉寂的靈感,涌起創作的沖動。我懷疑,這中間是否也有著某種宿命的味道。
魯院有很多貓,往屆學員中亦有多人寫過這里的貓,并稱之為“學術貓”、“幸福貓”。他們不但與貓進行過行為上的接觸,還進行過精神上的對話,彼此間似乎達成了某種默契。卻沒有誰專門寫過魯院的蛙鳴。我于是想,魯院的蛙是為我而鳴的。因為只有我能夠和蛙對話,能夠在彼此的目光和聲音中相互感應,完成穿越生命的交流。
不信你聽,“咕咕——呱,咕咕——呱”,蛙們叫得更歡了……
【魯院的蛙鳴的散文】相關文章:
沒有尾巴的魯魯童話故事11-15
魯豫的經典臺詞02-17
魯姓的起源與家譜03-29
《波魯魯冰雪冒險》觀后感01-26
關于魯達的歇后語03-31
《嘲魯儒》李白唐詩的鑒賞06-01
《波魯魯冰雪冒險》觀后感_600字01-22
特魯得太太01-21
魯公女全文11-04
補鞋匠邁爾魯夫的故事0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