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道經(jīng)典散文
“列車長(zhǎng)又長(zhǎng)啊,帶來(lái)民族希望呀····”聽著這首藏曲,心也隨著那列車長(zhǎng)長(zhǎng)的身形,飄向了遙遙的異地他鄉(xiāng),開始了流浪的漂泊。面對(duì)著一條生活的路道,它能有多少厚度,可以承載過(guò)往的行人及車輛的零碎腳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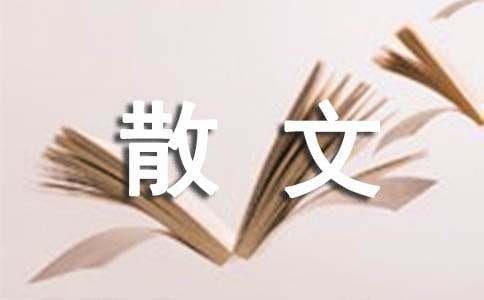
不平的坡坎,積水的洼坑,還有著無(wú)數(shù)的荊棘與無(wú)限的彎道,有誰(shuí)又曾在意過(guò)它的傷痛,面對(duì)著數(shù)人的踏踩、車行的超載,它沒(méi)有呻吟,也沒(méi)有喚吟,只是獨(dú)自的在那默默承受,承受著路人的踐踏、碾壓的百孔千瘡般的疼痛。
因?yàn)樗肋@就是生活,這就是自然所賦予路道的神圣職責(zé),它沒(méi)有理由去呻吟,也沒(méi)有幽怨的理由,去埋怨行人的歧唾。
這就是生活,這就是路道,選擇了路道,就是等于是選擇了一種別樣的生活。大千世界幽幽的路道是何其之多,又是何其之少,有多少人,行走在這樣的遙遙路道,又有著多少的路道,能記得行色匆匆的過(guò)往及行人。
記得在第一次聽到陳星的“打工十二月及望鄉(xiāng)等”歌曲專輯的時(shí)候,那也是在一個(gè)在異鄉(xiāng)流浪而又漂泊的生活。
在當(dāng)時(shí)聽到陳星的歌,就似聽到了一個(gè)知已的絮語(yǔ)在悠悠的訴說(shuō),訴說(shuō)著一顆顆心的孤苦漂泊而又流浪的落寞,終有了一處可以暫且停泊的彎道,可有了暫時(shí)心緒沉淀的寧心思索。
路的本身TA不會(huì)言語(yǔ)也不會(huì)訴說(shuō),TA只有靠人心的思索去會(huì)悟,每一條路道都有著不同的彎道,也有著不同的嶇道,更有著無(wú)邊的不同景色。
選擇了不同的路道就會(huì)看到不同的景色,沿途的風(fēng)景可能有美圖、也可能是齷齪、更可能是一道漫漫毫無(wú)邊際的黑色,是什么樣的風(fēng)景,其間又會(huì)有著什么樣的路道,我想這就區(qū)別于個(gè)人的心境與視野,是帶著一種什么樣的.心力與色彩或帶有著一種怎樣的豁然與達(dá)觀釋然的心境,而呈現(xiàn)不同的景致與面貌。
但是,對(duì)于路道要抱持以一種什么樣的心境與態(tài)度去認(rèn)知和把握,這又是個(gè)人不得不為之思索的問(wèn)題。
在于丹解讀《莊子》心得之三里去細(xì)品會(huì)悟“感悟與超越”的故事,或許更能得到形象而又具體的詳述、禪悟出精確的路道。
其故事是說(shuō):一大清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時(shí)候,在鎮(zhèn)江金山寺,他問(wèn)當(dāng)時(shí)的高僧法磐:“長(zhǎng)江中船只來(lái)來(lái)往往,這么繁華,一天到底要過(guò)多少條船啊?”
法磐回答:“只有兩條船”。
乾隆問(wèn):“怎么會(huì)只有兩條船呢?”
法磐說(shuō):“一條為名,一條為利,整個(gè)長(zhǎng)江中來(lái)往的無(wú)菲的就是這兩條船。”
對(duì)于此,司馬遷在《史記》中說(shuō)過(guò):“天下熙熙攘攘皆為利來(lái),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除了利,世人的心中最看重的就是名了。
多少人辛苦的奔波,名和利就是最基本的人生支點(diǎ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