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關推薦
一抔黃土憶親人隨筆散文
清明前夕,一大早,我還沒有起床,就接到了父親從老家打來的電話,他要我提前回去一天,說我義德叔的墳要遷入新的地方,讓我盡快趕回去幫忙,我滿口答應了下來。放下手中的電話,我的思緒卻久久地難以平靜,腦海里滿是義德叔的影子,悠悠往事像無聲的電影鏡頭一樣,一幕幕地閃現在眼前,一下子把我拉進歲月的回憶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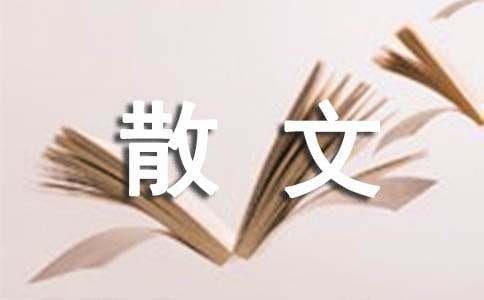
說起義德叔,算起來,他已經離開我們三十多年了。我印象中的義德叔,中等身材,一雙明亮有神的眼睛,鑲嵌在國字型的臉面上,他一笑起來,總是給人一種親切和溫和的感覺。
記得母親在世的時候,經常給我提起義德叔,說義德叔比我的父親小兩歲,他是我父親兒時最好的玩伴,兩個人經常一起到村西的小河里洗澡,捉魚;經常一起到臨近的幾個村子的小樹林里掏鳥窩;經常在一起捉迷藏,玩游戲;放學后,一起到地里去打豬草。那時候的生活條件雖然很艱苦,但他們在一起玩的卻很快樂和高興,故鄉的角角落落里,都留下了他們童年的足跡,兒時的歡笑聲。義德叔和父親一起度過了幸福的童年和少年時光。
記得父親說過,在他剛成家的時候,去了公社組織的打井隊工作了,當時我家里的情況,父親是家里唯一的男勞力,在打井隊會給一些生活補貼,可以緩解家里的燃眉之急,為了家里經濟條件能夠改善一點,父親不得不離開家。那時,我的爺爺有病臥床,姑姑們都在上學,我的年齡還小,父親去了井隊,家里的重擔就自然而然地壓在了奶奶和母親身上。義德叔那時還沒有成家,父親因為在打井隊里工作,不能經常幫著家里干活,義德叔忙完他家里的活后,經常會跑到我家里,問奶奶和母親,看看有什么需要幫忙的。那時村里人吃水,都要到村口的老井里擔水吃,記得那時我們村里有兩口老井,一口在村東,一口在村西。兩口老井供給著全村人的生活用水。記得天還沒有亮的時候,不少的鄉親們都起來了,他們擔著水桶,走向村口的老井里打水,木桶碰撞著井壁,發出悶悶地聲響。挑水的鄉親來來回回地人流穿梭,不停地相互間打著招呼。在穿梭的人流中,往往能看到義德叔的身影,父親到井隊工作以后,我們兩家人吃水的事情,他一個人主動承擔了下來。為了兩家人能夠及時吃上甘甜的井水,義德叔每天早上起來的都很早,他常常要跑兩三個來回擔水,常常累得滿頭大汗,可義德叔卻沒有一點怨言,也從來沒有喊過一聲累。我至今仍記得母親常說的那句話:“你父親在井隊工作的那段日子,多虧了你的義德叔幫助我們家啊。”義德叔的身影,行走在歲月的風塵中,伴隨著我們度過了每一個春夏秋冬,一直留在我的記憶深處。
后來,義德叔成家了,他到大隊開的飯店上班了,他也不用擔心我們家的吃水問題了,我的姑姑們長大了,能夠擔水了,打井隊解散了,父親從打井隊回來了,能夠幫著家里干活了,父親和義德叔又能天天見面了。義德叔在飯店工作以后,他隔三差五的,總是能帶一兩個燒餅回來,或者是水煎包包。他每次走到我家門前,總會順便給我留下一個燒餅,或是幾個水煎包包給我吃。有時,他會把我高高舉過他的頭頂,慢慢地就地轉起圈圈來,渾身都是自在的,時常逗得我哈哈大笑。記得那時候,在我們農村,吃的最多的還是紅薯面饃,玉米餅子,喝的大多是紅薯湯,玉米糊糊,能夠吃上白面饃是莊戶人家心中的夢想。記憶中,我吃著義德叔給我捎回來的燒餅或水煎包,是那樣的好吃,那燒餅的味道和水煎包的味道是那樣的美味,那美味像在我的心里扎下了根一樣,讓我至今念念不忘。
人的一生,誰也無法預見自己的未來。本來,義德叔有了家,娶了懂事賢惠的義德嬸,不久后又添了一個女兒和兒子,家里的生活雖然清貧,但一家人卻過得幸福和快樂。我們兩家住的不遠,常常能聽見義德叔一家人的歡笑聲從院落里傳出來。然而,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記得有段時間,義德叔老是在去飯店的路上戴著口罩。母親問義德嬸怎么回事情,嬸嬸說近段義德叔老是咳嗽,怕是著涼了,戴口罩是為了讓他避避風和涼氣。事情沒有想的那么簡單,直到有一天,義德叔咳嗽出了鮮血,一家人慌忙起來,趕緊和義德叔一起到縣里醫院檢查,縣醫院的醫生檢查后,建議義德叔到大醫院去做進一步的檢查,義德叔他們就到了鄭州,經過省城醫生的認真診斷,義德叔被確診為肺癌晚期,連動手術的機會和希望都沒有了。義德叔只好回來進行保守治療。說是治療,那時候的醫療水平還很低,遇見絕癥就是被宣判了“死刑”一樣。義德叔得病后,一家人像被籠罩在一片愁云之中,家里的歡聲笑語不見了,一家人,就義德叔一個強壯勞力,家里家外的事都離不開他,義德叔就是家里的主心骨和頂梁柱啊,義德叔如果倒下了,這個家怎么辦呀?家里還有一位年邁的老母親需要照顧。義德嬸見到我的母親,說起來的.時候,她常常以淚洗面,哀聲嘆氣,母親也是陪著她一起掉眼淚。父親經常跑過去看義德叔,盡量安慰著義德叔,哥倆還是那樣的親,哥倆的話還是像小時候那樣說不完,可父親的心里總是酸酸的,沉沉的感覺,父親卻一點也不能在義德叔面前表現出來,那種滋味,那種兄弟深情,只有父親自己知道,父親多么希望義德叔好起來了啊,一家人離不開他呀,我們大家都離不開與人為善的義德叔啊。
無情地病魔侵襲著義德叔越來越弱的軀體,他連下床的氣力都沒有了,昔日明亮有神的大眼睛深深地陷了進去,看上去骨瘦如柴的樣子,再也看不見他為我們家擔水時,穩健有力地步伐了。義德叔走了,在家人的哭泣聲中,帶著對家人和親人的牽掛,帶著對這個世界的無限眷戀,到了遙遠的地方,最終化作了故鄉的一捧黃土。
義德叔走后,父親沒有忘記他的囑托,我家,我大伯家,還有義德叔家,每年麥收的時候,我們三家都在一起收麥,打場,互幫互助,共度難關。平日里,有需要縫縫補補的家務活,母親經常幫義德嬸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她的幾個孩子和我一樣,在冬季還沒有來到之前,就早早地準備好了過冬的棉衣。
隨著歲月的流逝,義德叔的兒女長大了,都有了各自幸福的家庭,義德嬸卻明顯地老了,早早地,滿頭的青絲平添了不少的白發。前幾年,義德叔的兒子帶著義德嬸去新疆打工去了,家里的房屋和院落的大門都落了鎖。每次回老家,路過他家院門前,我看見那一把大鎖,心里總是感慨萬千。我曾經多么熟悉的院落啊,一把大鎖,鎖住了小院里所有的光陰故事,鎖住了失去親人的悲傷和難言的落寞。鎖上的斑斑銹跡,滿綴著時光的烙印,和對義德叔的思念。
義德叔的墳地,最早在我老家的自留地上。隨著近幾年鄉村的發展,自留地上都蓋成了樓房,有了新的住家戶,村里要求所有自留地里的老墳都要遷走。記得遷墳那天,天陰沉沉的,像我們一樣沉重的心情。我和義德叔的兒子,攙扶著已經滿頭白發的義德嬸,輕輕地走到了義德叔的墳前,義德嬸說:“老頭子,我來看你來了,我兌現了給你的承諾,我沒有再嫁,一直伴你終老啊。咱們母親走的時候很安詳,孩子們也都成家了,還有了孩子,都好著呢,你就放心吧。你現在要搬新家了,慢慢走啊,等我......”義德嬸說的時候,神情是那樣的平靜,看不出一絲的悲傷感,也許,義德嬸已經沒有眼淚了.三十幾年的風風雨雨,她帶著孩子都挺過來了,一路走來,一路艱辛,一家老小,孤兒寡母的,內心的憂傷和痛苦,只有我的義德嬸嬸心里最清楚了。此時,沒有人能代替她內心的痛和傷感。
當義德叔的墳被挖開的時候,父親再也抑制不出內心的悲傷,失聲痛苦起來,昔日的玩伴,可親的義德叔,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已經腐朽的棺木和他的枯骨。無情的歲月啊,你帶給了我們多少的憂傷和痛苦啊。
我用我的雙手,虔誠地捧起一捧新土,輕輕地撒在義德叔的墳頭上,新鮮的故土,滋潤著義德叔曾有的汗滴,融入我綿綿無盡的思念,像一床厚厚的棉被,護佑著他老人家安然入眠。望著義德叔的新墳,我深深地給義德叔三鞠躬,表達我深深地哀思。義德叔,我的父親給我說過,我的名字就是您給我起的,我的名字就是我生命的符號和印記,義德叔就如同我生命的符號和印記一樣,已經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里。
【一抔黃土憶親人隨筆散文】相關文章:
憶散文11-11
憶草場散文11-27
憶如隨風散文11-17
憶浙東才女短文散文11-11
散文:被親人牽掛真好11-19
想念遠去的親人散文05-01
拾憶冬日茶香散文12-15
墜憶如冰散文欣賞11-09
暮與憶瘦了誰散文11-07
夢見散文隨筆0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