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鎮弋江散文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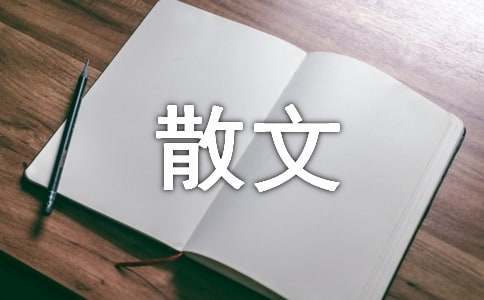
青弋江頭一葉舟,山光云影共沉浮。
門前多是桃花水,未到春深不肯流。
這是流傳了好多年的古代詩歌,把個小鎮活色生香起來。
小鎮叫青弋江,就是那條水的名字。后來簡易了,也可能為了區別于水域,就喚做弋江。
弋江小鎮在皖南。
在杏花春雨里,馬頭墻和烏篷船在拂曉或黃昏里影影綽綽,而彎彎曲曲的石拱橋風韻不減,當年的船工號子落在水面,叫水也時而粗獷時而溫情,山野小調被紅頭巾拉得細長柔韌,卻猶然在耳,夜夜在恍然間響起。
黛綠的珩瑯山是她高尚而莊嚴的剪影。
她被一彎600余里的清澈徽水摟在懷里,溫濕了很多個世紀,以及奇峰沃野了。
被方圓十里蓊蓊郁郁,且有脆生生疏響的柳葉和修竹滋養、潤澤著。
柳蔭與幽篁交織的綠的光影里,是一條銀蛇似的蜿蜒曲折的小道。小道兩旁匍匐叢生著,被連年春風喚回,卻又綠了又黃,黃了再綠的野草。腳下是沙質的泥土,間或有大小、顏色和形狀各異的石子,絆了行人的鞋子,甚而至于鉆進腳丫里。只是它始終清爽,不像泥土那樣纏絡人的腳步。
還有就是依河而建的民宅,如今主要分布在新正街、湯蓬街,大多是古老的、格調和風格整齊劃一的徽派建筑,無外乎馬頭墻、天井、木板小樓,和鏤花窗欞。正屋往往能夠見到一張八仙桌,兩旁是竹木椅子。中堂一般是已經泛黃的有些個年頭的國畫,畫面以福祿壽和山水居多。通文墨的和有些頭臉的人家,多是宣紙裝裱的真跡,尋常人家也就是復制印刷的了。雖然有傳說說,虎踞中堂,家破人亡的,可是仍然有人家掛老虎的,且多為下山虎。我思量可能因為下山虎可見老虎正面的緣故。這一切的氛圍都是靜默的,沒有鮮活的色彩,相對就遜了生氣。可是,這并不打緊。因為真正的風景是隱藏在窗簾后面的,倘若因風而起的話,不經意間,我們可以瞥見一掠而過的花襯衫,裊裊娜娜的身影,以及長長的、搖曳的發梢。如果再近些,還有可能嗅聞到女孩兒家身上的香水味。它們一般都是非常濃郁的。書里記載,過去皇宮禁苑有金屋藏嬌的故事,而在皖南的民間,也有這般木屋藏驕的,只是他們一直沒有修煉成很好的那種氣量,也羞于自夸顏色。不溫不火,含蓄內斂,是他們一貫的風格,雖然因此沒有成就什么氣候,卻也能夠平平安安,得以使一脈香火傳承。
新中國杰出的革命家、外交家王稼祥少年時,就曾經住過這里的有著天井和小木樓的屋子。彼時,他16歲始從涇縣厚岸老家外出讀書,在距離小鎮16公里的南陵縣城的教會學校——樂育學校。他的父親王承祖早年在小鎮開當鋪,門面有10余處,是個遐邇有些名頭的商人,家資因此而殷實。相傳他的兩個姐夫翟紹元、吳子松也在此當朝奉。可惜,已經沒有足夠確證的文字資料了。
二
新正街的碼頭口有好多老樹,枝干盤旋,郁郁蒼蒼,往里走幾步,右側相傳有個四方形的,既像牌坊又像城門的建筑,便是洞子口了。街坊里巷均認為“天一閣”三字,系東漢末年吳國孫權手下的重要人物,當年在青弋江上操練水軍時的領導人魯肅親筆題寫。因年代久遠,墻面滿是青苔,黑魆魆的,一入洞口,涼風習習,即便盛夏也清涼。我孩提時代,也就是前40年,常常走過那個地段。所見所聞雖然沒有傳說的那樣神奇,也不見了那魯子敬的手筆,可是情景鄉風卻也依稀仿佛。
與湯篷街相鄰的沙河溝,有一座拱形石橋,名為貽谷橋.橋寬4米,連接著南北兩岸人家。有圖方便抄近路的店家,在后門口搭一塊長長的跳板,凌空架于河溝上。欲出后門,從跳板上便可從容走過。每逢訊期,弋江河水猛漲,往往瀉入西街的大塘里,過往的`舟楫便泊于此,形成一處奇特的風景。古老相傳這個沙河溝,原就是一彎淺淺的水溝,據說用這兒的水洗明姜,特別鮮嫩。抗日戰爭時期,日本鬼子經常用飛機扔炸彈,硬是把這兒炸成這樣。
在過去,水碼頭占了地利,商貿發展迅速,一般是比較繁華的。聚居的、流通的人多了,屋子自然就多了,多到一定程度就成為街市、乃至集鎮。唐代的詩人顧況在一首《青弋江》的詩歌里吟詠:“凄清回泊夜,淪波激石響。村邊草市橋,月下罟師網。”是可見想象往日的情景的。
據《南陵縣志》卷九載:“一統志在縣城東四十里青弋江上,漢置,后漢省建安三年,孫策平定宣城以東,二十年孫權使蔣欽屯宣城,即故城也。晉太康二年于宛陵縣置宣城郡,后置宣城縣屬焉。隋初,改宛陵為宣城,而故城遂廢。”還有,“章懷太子曰,宣城故城在今宣州南陵縣東。”可以想知,在東漢末之建安二十年,亦即公元215年,宣城故城,即古鎮弋江,便有了筑水而居的百姓,有了初具規模的“故城”。這時開始,小鎮有了文字記載的歷史,只不過至隋初因“改宛陵為宣城”,削弱了“故城”的發展勁道而已。
在皖南的青弋江流域,像弋江鎮這樣的水碼頭還有涇縣的章渡、赤灘,蕪湖縣的西河、灣址,除了灣址因為是蕪湖縣府所在地,如今依然繁華外,其他的幾處,已經日甚一日地不及陸路集鎮發展之快了。臨水小鎮在發展經濟的跑道上漸趨沒落,久而久之就能勾起一種懷舊的心理。小鎮于是搖身一變成為一冊冊線裝書,古色古香,在每年梅雨來臨的時候,最好散發出霉變的氣味來,再保留一些籬墻院落,貼上牛屎巴巴,遠遠近近傳來牧童短笛的聲音,炊煙裊裊,農村大嫂用地道的鄉音,叫喚晚歸的孩子:“小安(音)妮”,或者“小妹妮”,“吃夜(讀作ya)飯啰!”
三
其實進入天一閣就是進入老街了。老街原是用青石板鋪成的,石縫間可以淤積少量的水,時間長了就生長出幽幽的寸草來。后來老街發展了與時俱進了,也就成了如今的水泥路面,解放后更名為一個光鮮的大路貨名字——新正街。從碼頭口往西到西街頭的電影院,大約有2000米吧,這兒曾是十室九商的商貿中心。
傳說這條街是火龍地,大碼頭關口上面,留有兩個圓洞穴,即是火龍的一雙眼睛,所以過去的老街絕不允許開鐵匠鋪,因為打鐵必須起爐拉風箱,鐵錘叮當響,這樣便捶打了龍身,必然引起火龍的憤怒,火龍龍顏大怒了,就會降下火災。因此,鎮上不知起源于何時,也就是在每年農歷4月15日,都要祭祀火神,舉辦火神廟會。具體情形,我是沒有福分親見的了。只是在夏夜納涼的老樹下,老人們搖做芭蕉葉,說古時會零零散散地聊上一段,興趣好時就說的多,可以到夜涼如水,明月漸沉;興趣不好時,逼急了,還會討沖。
關于火神廟會的節目,相傳頗為豐富。有唱戲的,不知具體哪種?在皖南南陵,民間比較流行的是黃梅戲,廬劇,俗稱“倒到戲”的,名角是個叫周小五的,大約20年前,朋友“三歪子”曾經在南陵東門劇場請我看過他的《小辭店》。南陵本地有一種“目連戲”,號稱戲劇活化石。聽說正在申報非物質文化遺產,也不知究竟如何!最受歡迎的互動節目是玩龍燈,踩高蹺,抬臺角,挑花籃等群眾性喜聞樂見的文體活動。那一天,四鄉八鎮的趕廟會的,就像梅雨季節的潮水,一下子涌過來,老人們估計總在萬余人,把個小鎮瞬間擠得滿滿的。
我后來分析,估計廟會之所以如此紅火,一定是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的緣故。由于弋江鎮的水碼頭地位,山里的市縣,如涇縣、旌德、太平等地的商賈,順青弋江泛一葉扁舟,或者是山里的竹排、木筏,載著茶葉、柴炭、冬筍、香菇等土特產,是極順便地下來了。
弋江鎮本身沒有多豐富的木竹資源,可是那些年,那兒有一個皖南最大的木竹集散地。水里檣櫓競發,帆影聯翩。岸邊,竹木器制作業也異乎尋常得發達。從沙河溝到油炸灘,綿延數里,是竹木制品商貿一條街,1969年建造的老大橋下以致往北,是竹木原材料市場。最富特色的竹制品有:竹籃、筲箕、挑籮、細篩、曬扁、魚簍、竹椅、涼床、竹囤、竹墊、雞罩、烘干罩等生產生活用品,只要能夠想到的,就可以買到。尤其是其中的竹墊,乃是選取上好的水竹,剖成極細的線似的篾,在大姑娘、小媳婦的手里懷中纏繞跳舞,不到半日功夫就成了。竹墊正面有各色各樣的花紋圖案,講究的還可以編織出文字來。這種竹墊不可以折疊,只可以卷起來。如果夏季初用,需要用粗糙的毛巾搓洗,去除細篾的毛刺,否則是要傷了肌膚。因為竹子性涼,避暑的效果是可想而知的。在過去酷夏的日子里,幾乎每家每戶每張床上,都是有這樣的竹墊的。大元邱是鎮上的一個自然村,估計有幾百人家,對這種竹墊的制作最是考究,名氣也最大。不僅女人們精于此道,大老爺們也個個可以露兩手。曾幾何時,編織竹墊是他們家庭的主要經濟來源。上個世紀80年代,在我的印象中,弋江鎮的竹墊好像還漂過洋出過海,掙過外幣什么的。到弋江鎮去,誰家不帶回一個竹籃、筲箕,或者竹墊呢!那是遐邇聞名的竹編之鄉啊,可惜已經風光不再了!也許都是空調惹得禍吧……
【古鎮弋江散文】相關文章:
哭泣的永樂江散文05-03
記家鄉的三江釣客散文11-03
古鎮老街作文03-07
沉江07-09
涉江07-09
我將枕著烏蘇里江的濤聲入眠散文11-05
江郎才盡的江淹07-17
《全宋詞》江 衍07-04
江淹《別賦》12-03
江雪古詩全文08-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