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在童趣鄉情中散文
不知是啥原因,現在過春節總覺得有點兒失落感,辛苦地勞作了一年,好不容易盼得幾天稍長的假日,卻被絡繹不絕的無聊的“應酬”占據了,不是你約我請,便是排在打擂似的“炮臺”上比闊——誰的爆竹花色多、價格高、放得時間長,誰便顯得最富有……實在是單調而乏味,自然,過年的味兒便淡了許多,甚至有時,讓人產生厭煩感。這與我們小時侯過年是迥然不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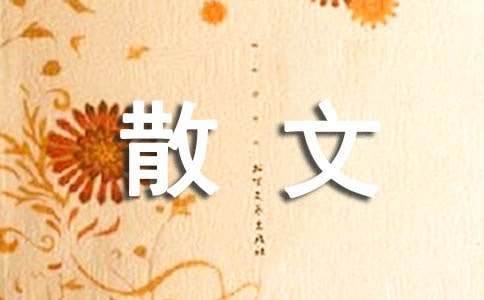
記得我小的時侯,物質條件與現在比起來,真是相差遙遠,可過年卻真有一種實足的“年味兒”。我生在一個地道的小山村里,村里人口不多,老幼共計亦不過百十來口,可過年卻比現在熱鬧得多。一到臘月,農田里的活計便基本上收拾停當了。農家們早已趁天未大冷,向地里積足了一堆一堆的糞肥,只等來年春天撒到田里去,或是修補一下塌倒的墻堰,以便于來年開春時播種。這兩項工作都是在隆冬農閑時完成的,把糞肥從農家運到田里去是輕壯年和少年兒童的事,每人背一個合身的竹簍,由南嶺背到北洼,或由東坳運到西坡,夾在運肥的隊伍中,聽大人們說笑,真是一種很愜意的事兒。我那時八九歲,雖掙的工分不多,但每年寒假便爭著參加。小隊長看我愛干活,便破格地給了我每天兩分五的工值,這對于我來講已不單是一種鼓勵,簡直是一種榮耀,因同齡的孩子每天只有兩分。其實,我參加勞動的真正原因倒不是勤勞,而是喜歡這種集體活計的氣氛;修補倒塌的墻堰是老年人的任務,三兩人結成一組,我在七八歲的時候是經常隨爺爺出工的,爺爺的搭檔是一位姓耿的老爺爺,看上去年齡比我的爺爺要大些,他說話和善也很幽默,他和爺爺從抗日時期便是最好的搭檔,都是抗日小區隊伍中的主力,我特別愿意跟在他的屁股后面,每次得到這樣的機會,我便不失時機地求他講炸炮樓、送信等抗日游擊的故事,他也顯得很激動很認真,每次都讓我聽的心曠神怡。
地里的活干完了,臘月也基本就到了,這時也便成了鄉親們節前忙碌的開始。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各有各的活計。壯青年的小伙子一早一晚便會背著山也似的劈柴捆兒從羊腸小道間蹣跚而歸,把柴捆兒碼成整齊的方堆,大人們說這是預備做豆腐用的;備年貨一般是由家中的婦女承擔。磨年米、蒸年糕,發豆芽、做豆腐等事情都須提前搞定。
磨年米是用石碾完成的,把大黃米倒在碾盤上,插幾根推磨用的碾棍,家里的成員輪流地扶在上面,并順著那瓷丁丁的碾道邊聊天邊推磨,現在想起來真可以說得上是一種最具有娛樂性的健身活動了,這項活動也是孩子們最搶著干的,他們經常采用的方法是“快速淘汰賽”——四個孩子先扶在碾棍上做好準備,聽到當中的一個人喊道“預備……開始!”碾跎便在碾盤上飛快地跑了起來,隨著轉速的加快,便會有人被甩出碾道,直到只剩下最后的一人,于是,這個“幸存者”便毫不客氣地以勝利者自居,挺胸抬頭,神情激昂,并一準兒會馬上組織第二輪的比賽。
年米磨得后,便是蒸年糕,這項工作的全過程我記得不是太清楚,但在制作之前,必得要做一些準備。那時侯沒有蒸鍋、籠屜之類的廚具,更沒有微波爐等現代化的東西,因此,做年糕是用一種叫做“糨蓬”的傳統農家廚具來完成的。糨蓬的原材料是一種名曰“高蒿”的長草,形狀有點象馬尾,呈棕黃色,這種草的生命力很強,嚴冬季節,別的草木都已枯萎,但這種草卻很茂盛,只是略微有點發干,每年一到隆冬季節,爺爺便會到山上去,打回磁磁實實的一大捆山草,然后浸泡在水里,第二天撈出將水分空走七八成,這時就可以開始打編了,爺爺打編的速度很快,不到一頓飯的工夫,一件精致的糨蓬便會安然落生。這種廚具的用途是為了蒸年糕或蒸饅頭時保溫和防止水分流失,糨蓬的形狀極象南方漁民頭上戴著的蓑,只是沒有頂端的尖兒,而是一個直徑約拳頭大小的圓孔,蒸年貨時,用毛巾將頂端的孔堵嚴,而出鍋時把毛巾一揭,將鍋內的高溫氣體一放,便可用手握住頂孔的邊緣將糨蓬取下,這時,一鍋熱騰騰香噴噴的年糕便出世了,隨著熱氣的升騰和擴散,隔不了多會兒,便會有四五個小手凍得象包子似的頑童聚集在鍋臺的周圍,摩拳擦掌地吸允著四溢的濃香或使勁地從蒸汽的縫隙間窺望著鍋里那招魂的年貨,這時,不管是誰家,主廚的老大娘或少婦人一準會樂滋滋地端來若干個小碟子,用刀將年糕切成若干個大小一樣的方塊兒,分發給孩子們,而這些孩子們接過了盤子即會狼吞虎咽地大吃起來,那時,我是經常夾雜在這種隊伍中的,現在回憶起來那種甘甜幽香的味道真是叫人咂指難忘。
發豆芽是老家人所備年貨中最基本的活計之一。那時,村里人睡的都是土炕,無論是來人,還是會客,都是圍坐在小土炕上吃茶聊天,那暖洋洋的滋味會自然地給人增加幾分快慰和陶醉,同樣,這小小的土炕也便成了農家人制備年貨所不可缺少的“工具”。豆芽便是在土炕上培植出來的。老人們將作豆芽的原料(黃豆或黑豆)精心地挑選出來,培植在一口大瓷盆里,用木蓋蓋好,然后將其放在炕頭上,放的位置是有講究的,溫度不能過高,也不能偏低,要保持適中,盆上還要蓋上一層厚厚的棉被,以保持濕度。在我家,奶奶是樂此不疲的,每天早晚她都要調一調豆芽盆的位置,或檢查一下豆芽的生長進況,我經常見她有時一邊用手撫摩著豆芽盆,一邊象是對著自己的孩子似的說:“快點長吧!要長得滾滾胖胖兒,可別長得細細長長兒”果然,大約六七天之后,一盆膀闊腰圓的'豆芽便擎舉著厚厚的木蓋健康地出世了!
不知是天意還是湊巧,每年春節做豆腐的時候都是很冷的時候,但盡管如此,小孩子們依然會非常亢奮地尾隨著大人并冷不丁地幫點倒忙,真叫人啼笑皆非。
做豆腐是全家性的行動,首先在院子一邊搭起的土灶上會支起兩口巨型的大鍋,每口鍋里添上五六桶水,一般到鍋的六七成水位,然后釜下加柴點火,約莫個把鐘頭,當能見到小火苗舔著鍋底,大水花在鍋里來回翻滾時,便是加入已磨碎了的豆瓣的時候了,然后,再經過攪拌、榨汁,蒸發、點漿等工序,于是,一道顫悠悠香噴噴的農家豆腐便成功地完成了。那時,村里不管是哪家,在這天的晚上必會辦一桌豐盛的“豆腐餐”作為節前“演習”:炸豆腐泡兒、香椿芽拌豆腐、豆腐木耳黃花湯……
進入臘月,越是貼近春節,孩子們的心情越是急切,并開始掰著手指頭掐算起了日子,在我的幼年,老家流傳著一首童謠就是表達了這樣的一種對年的渴望和期盼的心情:“二十一刷屋里,二十二帖畫兒,二十三糖棍兒粘,二十四寫大字,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宰豬肉,二十七殺公雞,二十八白面發,二十九全都有,三十兒白面包子去了皮兒,初一早吃個餃……”
“刷屋里”是老家過年的必辦之事,根據家里的境況刷墻所用的涂料也不一樣,家里有錢的,從供銷社買回幾斤“大白”,而沒錢的人家,便要到三四十里以外的山上去掏一種叫做“白土粉子”的東西做刷墻的涂料。我家屬于刷白土粉子的那一種。別看沒人家豪華,但望著重新粉刷過的墻壁,卻絲毫沒有遜色于人的感覺。倒頗有一種喜悅的心情,第二天,大人們便要貼年畫了。我記得很清楚,奶奶和媽媽每到這個時候,就會小心地將卷著的一張張年畫攤在桌上,歪著腦袋逐個欣賞,然后再把它們貼在墻上,我特別喜歡追著他們干這些事,哪怕能討到一個遞糨子的差使也非常高興。墻上的畫五花八門,我記憶最深的一幅畫叫“牽龍”,畫面上是一條綠色的蛟龍被一位頭頂草帽、穿一件家做背心的健壯青年用一根長長的鐵索牽著鼻子在走。上面還寫著幾行字:“叫你走,你不敢站;叫你快,你不敢慢;叫你發電就發電!”當然,那時我還不認字,是聽姐姐總是念,才不經意記住的,我特別喜歡這幅畫,但有的地方不太理解便去向姐姐討問,姐姐很神秘地對我說:“這條龍犯了天規,得罪了玉皇大帝,然后玉帝就派天兵天將下海去捉拿它,捉住后就把它交給了畫上的這位叔叔,由他看管,當然是讓它怎樣就怎樣了!”之后,我經常站在這幅畫前發呆,因為我很羨慕畫上的那位叔叔,更想得到一副象他那樣的鐵索……有時,望著滿墻的年畫,我會顯得很出神,因為在當時媒體形式極少的情況下,這些便是最具有吸引力的東西。
其實,真正叫孩子們陶醉的還得數除夕和年初一。
除夕之夜,孩子們盼望已久的時刻終于來到了,他們會打起自制的燈籠,將成鞭的爆竹拆成單個的小炮,慢慢地省著放,他們或是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或是由大人們領著,找一個寬敞的地方去完成放炮這項“神圣”的使命,我那時最喜歡讓小叔帶著我,和我一起分享快樂,小叔長我六歲,對我很好,每到年根兒便會偷偷地為我準備些不同品種的炮竹,等到三十晚上那當兒,突如其來地將其塞入我的手上,給我一個大大的驚喜,小叔給的炮種類很多,有鉆天猴、閃光雷、宇宙火箭、大地開花、公雞下蛋等,放將起來,真是叫人目不暇接心曠神怡,比如,“宇宙火箭”那長長的尾巴經常會把我帶到一個非常神奇的幻想世界。
當孩子們搓著紅紅的小手回到屋里時,另一種高興的氣氛便會立即填補上來,媽媽和姐姐們早已圍坐在炕桌的周圍,用自制的撲克牌打起了“升級”,可不能小看這副自制的撲克牌,它可花費了姐姐的好大工夫:先是找材料,當然這材料的主要成分是紙,有時姐姐為了找到一些白而厚的紙張會訪遍親朋好友;材料找到后便是加工,加工的工序很煩瑣,首先要將紙張剪成一班大小的長方形,再用熬好了的糨糊把它們粘疊起來,然后風干、壓平;最后一道工序是筆工,即往空紙牌上填寫花色,這是個細活兒,每每都要花費姐姐近七八天的時間。等這副牌做好后,便也進了姐姐最珍貴的小木箱子,當然箱子是上了鎖的,除她自己時不常的拿出來欣賞欣賞外,是從不讓別人把玩的,更不會允許它上桌面,只能等到除夕那天才能公諸于眾。
每年春節我都是堅持要熬夜的,但每每都是我第一個敗下陣來,不到午夜我便會在極度的掙扎中進入夢鄉。等睜開眼時已經是大年初一的清晨,一家人早已圍坐成一圈兒有說有笑地在捏餃子呢。
聽老人們說,吃餃子之前,小孩們是須要先去拜訪“椿樹王”的。恰巧,大叔家的房子后面便有一棵很大的椿樹,旁邊還有一棵小椿樹牙子,姐姐很希望自己將來能長成一個高個子,于是,在一個年初一早晨她便舉意去拜訪,我再三請求,她才勉強答應帶我,我們按著奶奶的吩咐出發了。一路上,奶奶的話便成了最高指示,我們不敢回頭,不敢東張西望,徑直地朝著大椿樹走去,到達目標后,姐姐一下便抱住了那棵最大的椿樹王。我呢?只好學著姐姐的樣子將那棵小樹牙子摟住,按著奶奶事先教的“口訣”念叨起來:“椿樹王,椿樹王,你長粗,我長長!”可最拿這當回事的姐姐卻偏偏念顛倒了,念成了:“我長粗,你長長”,她急得直哭,并且更正了七八次后才悶悶不樂地回到了家里,可我卻很高興,因為和姐姐相比,我終于沒有出現錯誤。
……
唉!說起童年的春節,總有扯不完的話題,轉眼自己已過了而立之年,需要辦的事很多,需要想的題更雜,但我卻偏偏被童年的牽掛所纏繞而不能自拔。為此,我于去年特意回到了故居,但是那個村莊卻已不復存在,據說,已于十五年前集體搬遷了,人搬到哪里的都有,我所能看到的除了些倒塌石房的廢墟,便是被高草淹沒了的記憶深處那寬闊的大道……我的心在急劇地收縮,我一口氣從村口跑到了那間曾經養育我童年、鑄就我性格的小小的院庭,只見,石墻的斷壁上已長滿了幾尺高的蓬草,院落已被荒蕪了的植被所占領,我的腳步在這個不大的面積里徘徊著,這里的一切都是那樣地出乎意料,都是那樣地令人心痛……
我拖著沉重的步子向院外走去,突然,幾聲小蟲的“吱吱”聲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疾步跑了過去,蹲在那里仔細地尋找著,剎那間,幼時的情景一下子涌上了我的心頭。二十多年前,我剛七八歲時是經常到這里逗一種老家人叫它“鎖來兒“的小動物的,這種動物的巢穴只有拇指肚大小,是呈旋渦型的細砂窩兒,鎖來兒深藏在旋渦的底部,輕易不露面,但只要我們蹲在旁邊輕輕地說幾句:“鎖來兒,鎖來兒,開門來!”它便會伸出小腦袋來回擺動,表示歡迎。……我著急地在這塊不大的土地上搜尋著……啊!我終于找到了,找到了!只見離我兩米左右,一枚精致的小旋渦安然地坐落著,我輕輕地蹲在它的旁邊,用這種已失去童音和鄉音的聲調慢慢地說道:“鎖來兒,鎖來兒,開門來!你的好朋友來了!”說完后,我便焦急地等待著它的反應,可是一秒、兩秒…九秒、十秒……時間慢慢地過去了,卻總是不見它的出現。我正失望地意欲離開的時候,卻見細砂似有一絲的流動,于是,我目不轉睛地凝視著,只見,一個小小的腦袋緩緩地從旋渦底部鉆了出來,警覺而慢慢地朝四周望了望,然后才興奮地轉動起身體、搖晃起腦袋。這時,我的心一下醉了,淚水情不自禁地流了下來。我想,它可能真的是我的那個童年的“伙伴”,或是那個童年“伙伴”的兒子、孫子……總之,它們的親情教育是沒有中斷的。
這似乎終于教我找到了春節懷故的緣由了,原來,這里存放著我歡樂的童年和那永不能割斷的鄉情。
【年在童趣鄉情中散文】相關文章:
鄉情的散文10-31
那年在探家路上散文05-01
欣賞童趣札記散文11-03
鄉土 鄉情 鄉愁散文欣賞04-30
童趣說課稿11-04
鄉情高一作文08-18
《童趣》教案設計11-24
小學在困難中求散文11-14
靜從動中求散文欣賞11-04
農村女的愛鄉情0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