沱江邊的車夫散文
我努力想從眼前這車夫身上尋找沈從文當年回湘西時、那一路幫他將行李從沅陵挑至鳳凰的挑夫的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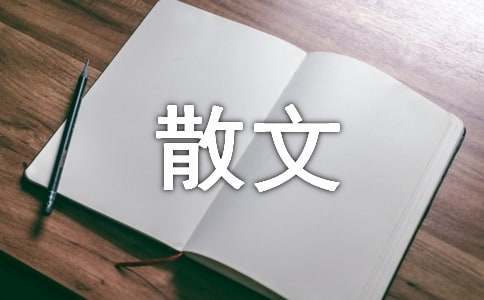
這是一個年近50的車夫,不高、黑,一件淺宗色大褂穿在上身,但他的上身和臉一樣,呈方塊狀;兩腿短小,顯得發育不良,走路的時候,容易讓人想到是兩根火柴棒架著個老大的火柴盒子在奔跑——這個比喻夠絕的。在當面和他說話時,看著他國字臉上的豐富表情,我有好幾次忍不住偷著樂。
他拉著我們在沿江窄窄的石板路上飛奔,不時跟對面來的人力三輪車用鳳凰土話嚷嚷著大聲招呼,不時回頭跟我們介紹沿途景物,同時沒忘了在會車時將行人吆喝到一旁:“車來咧——讓一讓,讓一讓啊——”
嗓門粗啞。如果不看他本人,你會以為這嗓門的主人至少年屆不惑了。然而他車齡并不長,大約在鳳凰開始大規模開發的2001年起,他就從事了這個行當。六年,他的嗓音和沱江邊所有車夫一樣,被打造成千人一面。
沈從文墓地我已經去過,可我還是想去,一是喜歡聽濤山依山傍水的清幽,二是這里有個村人用的'小碼頭,從此地可以乘坐本地人的小船泛舟沱江(俗稱沱江野游)。車夫聽說我們還想游沱江,立刻來了興致,執意要為我們介紹渡船。為著他可以從中拿點介紹費,我也沒有堅拒。這個拉了六年車的車夫,用一輛車,拉活了一個家。他的那雙手,還將繼續拉下去;他的雙腳,還將繼續丈量著這熟悉的青石路——生命中又有多少個六年呢?他的發家致富的夢,大約會始終在六年外等他。
我們在墓地耽擱了不少時間,下得山來,花衣服立刻迎了上來,原來他一直在等著我們。
他憨厚地笑著,太陽將他的臉曬得又黑又黃,他搓著大手跟我們介紹旁邊的船夫,那船夫比他稍年長,一樣地黑。似乎是為了價錢的緣故,兩人在小聲地商議。因是本地土話,我沒有聽懂,但是看得出來,花衣服在為我們斡旋,爭取了一個我想要的合適的價格。那一刻,我心底有些感動,他居然是個重義的車夫!
想起車停中途的時候,他為我們算的賬:每天拉客十趟,每月3000,遇到摳門的主顧或者旅游的淡季,還不到這個數。這筆看似不低的收入中要上繳一部分給旅游局,大部分維持家用恰好,還小有贏余,但旅游業的瘋長同時刺激了本地消費,比省城還高的的物價讓他離富有總是那么遙遠,想必他的日子過得十分節儉。
但他頭腦中卻又和我們一樣,有著很多計劃和憧憬。他不斷對我們絮叨,沿江這一帶一定會不斷發展,現在的遠郊以后一定會繁華熱鬧起來,那時,大約他也可以將車拉得更遠吧。
這個理想的樸實無華讓我長久地沉默,對二年里直線上升的車價,第一次覺得合情合理。
這沱江的車夫,分明仍是數年前的挑夫,漲價非他們所愿,生存卻始終是惟一的信念:只是這么簡單、安寧地生存著,黃昏回家時有滿院的煙火等著他,白天有車可拉,孩子聽話肯讀書,長大了不要和自己做一樣的事情。
這是真的,我聽過很多車夫在談將來把孩子送到外面去上大學的事情,甚至議論到將來每月給他們多少伙食費合適。
他們圍在老城門的城墻根下,一邊等客,一邊閑嘮嗑。他們大多是壯年的男人,少數女人偶爾頂替家中男人來拉上一兩趟,但絕不久留;她們更愿意去碼頭賣河燈或拉客,為自家或別的相熟的渡船鼓動七寸之舌介紹生意。
這些男人便有客拉客,無客時就侃大山,侃完國際局勢;侃最近肉價15元一斤,要吃不起肉了;又侃誰誰昨夜輸了幾十幾百被老婆罰跪搓衣板;侃到葷段子時,是他們最開心的時候,不免大笑一番,反復詢問若干細節,說的聽的都津津有味;侃到家中孩子讀書的事,瞬即恢復神色,收斂了滿臉的壞笑。
夕陽悄悄地挪移,曬著城墻根的青苔和小草,幾十年過去了,幾百年過去了,青苔依舊,荒草依舊,古城里的男人活得依舊:那么卑微,那么自在,那么滋潤,那么輕易地就滿足。
那個花衣服的車夫夾雜其中,他的孩子還小,離讀大學還有漫長的路要走,他有理由夢想更多,可他的夢和旁的車夫比起來,又并無不同。
【沱江邊的車夫散文】相關文章:
漫步沅江邊散文11-05
有關馬車夫的寓言故事11-12
《臨滹沱見蕃使列名》李益的唐詩鑒賞02-04
宿江邊閣 / 后西閣原文及賞析11-19
友情的散文08-22
土地的散文08-20
曾經的散文08-19
老屋的散文12-08
李樹的散文12-04
秋蟬的散文12-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