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關推薦
古文學的欣賞名家散文
新文學運動開始的時候,胡適之先生宣布“古文”是“死文學”,給它撞喪鐘,發訃聞。所謂“古文”,包括正宗的古文學。他是教人不必再做古文,卻顯然沒有教人不必閱讀和欣賞古文學。可是那時提倡新文化運動的人如吳稚暉、錢玄同兩位先生,卻教人將線裝書丟在茅廁里。后來有過一回“骸骨的迷戀”的討論也是反對做舊詩,不是反對讀舊詩。但是兩回反對讀經運動卻是反對“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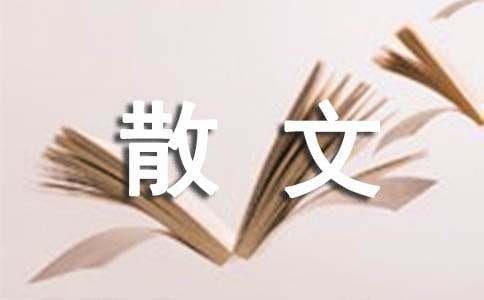
反對讀經,其實是反對禮教,反對封建思想;因為主張讀經的人是主張傳道給青年人,而他們心目中的道大概不離乎禮教,不離乎封建思想。強迫中小學生讀經沒有成為事實,卻改了選讀古書,為的了解“固有文化”。為了解固有文化而選讀古書,似乎是國民分內的事,所以大家沒有說話。可是后來有了“本位文化”論,引起許多人的反感;本位文化論跟早年的保存國粹論同而不同,這不是殘馀的而是新興的反動勢力。這激起許多人,特別是青年人,反對讀古書。
可是另一方面,在本位文化論之前有過一段關于“文學遺產”的討論。討論的主旨是如何接受文學遺產,倒不是揚棄它;自然,討論到“如何”接受,也不免有所分別揚棄的。討論似乎沒有多少具體的結果,但是“批判的接受”這個廣泛的原則,大家好像都承認。接著還有一回范圍較小,性質相近的討論。那是關于《莊子》和《文選》的。說《莊子》和《文選》的詞匯可以幫助語體文的寫作,的確有些不切實際。接受文學遺產若從“做”的一面看,似乎只有寫作的態度可以直接供我們參考,至于篇章字句,文言語體各有標準,我們盡可以比較研究,卻不能直接學習。因此許多大中學生厭棄教本里的文言,認為無益于寫作;他們反對讀古書,這也是主要的原因之一。但是流行的作文法,修辭學,文學概論這些書,舉例說明,往往古今中外兼容并包;青年人對這些書里的“古文今解”倒是津津有味的讀著,并不厭棄似的。從這里可以看出青年人雖然不愿信古,不愿學古,可是給予適當的幫助,他們卻愿意也能夠欣賞古文學,這也就是接受文學遺產了。
說到古今中外,我們自然想到翻譯的外國文學。從新文學運動以來,語體翻譯的外國作品數目不少,其中近代作品占多數;這幾年更集中于現代作品,尤其是蘇聯的。
但是希臘、羅馬的古典,也有人譯,有人讀,直到最近都如此。莎士比亞至少也有兩種譯本。可見一般讀者(自然是青年人多),對外國的古典也在愛好著。可見只要能夠讓他們接近,他們似乎是愿意接受文學遺產的,不論中外。而事實上外國的古典倒容易接近些。有些青年人以為古書古文學里的生活跟現代隔得太遠,遠得渺渺茫茫的,所以他們不能也不愿接受那些。但是外國古典該隔得更遠了,怎么事實上倒反容易接受些呢?我想從頭來說起,古人所謂“人情不相遠”是有道理的。盡管社會組織不一樣,盡管意識形態不一樣,人情總還有不相遠的地方。喜怒哀樂愛惡欲總還是喜怒哀樂愛惡欲,雖然對象不盡同,表現也不盡同。對象和表現的不同,由于風俗習慣的不同;風俗習慣的不同,由于地理環境和社會組織的不同。
使我們跟古代跟外國隔得遠的,就是這種種風俗習慣;而使我們跟古文學跟外國文學隔得遠的尤其是可以算做風俗習慣的一環的語言文字。語體翻譯的外國文學打通了這一關,所以倒比古文學容易接受些。
人情或人性不相遠,而歷史是連續的,這才說得上接受古文學。但是這是現代,我們有我們的立場。得弄清楚自己的立場,再弄清楚古文學的立場,所謂“知己知彼”,然后才能分別出那些是該揚棄的,那些是該保留的。弄清楚立場就是清算,也就是批判;“批判的接受”就是一面接受著,一面批判著。自己有立場,卻并不妨礙了解或認識古文學,因為一面可以設身處地為古人著想,一面還是可以回到自己立場上批判的。這“設身處地”是欣賞的重要的關鍵,也就是所謂“感情移入”。個人生活在群體中,多少能夠體會別人,多少能夠為別人著想。關心朋友,關心大眾,恕道和同情,都由于設身處地為別人著想;甚至“替古人擔憂”也由于此。演戲,看戲,一是設身處地的演出,一是設身處地的看入。做人不要做壞人,做戲有時候卻得做壞人。看戲恨壞人,有的人竟會丟石子甚至動手去打那戲臺上的壞人。打起來確是過了分,然而不能不算是欣賞那壞人做得好,好得教這種看戲的忘了“我”。這種忘了“我”的人顯然沒有在批判著。有批判力的就不至如此,他們欣賞著,一面常常回到自己,自己的立場。欣賞跟行動分得開,欣賞有時可以影響行動,有時可以不影響,自己有分寸,做得主,就不至于糊涂了。讀了武俠小說就結伴上峨眉山,的確是糊涂。所以培養欣賞力同時得培養批判力:不然,“有毒的”東西就太多了。然而青年人不愿意接受有些古書和古文學,倒不一定是怕那“毒”,他們的第一難關還是語言文字。
打通了語言文字這一關,欣賞古文學的就不會少,雖然不會趕上欣賞現代文學的多。語體翻譯的外國古典可以為證。語體的舊小說如《水滸傳》、《西游記》、《紅樓夢》、《儒林外史》,現在的讀者大概比二三十年前要減少了,但是還擁有相當廣大的讀眾。這些人欣賞打虎的武松,焚稿的林黛玉,卻一般的未必崇拜武松,尤其未必崇拜林黛玉。他們欣賞武松的勇氣和林黛玉的癡情,卻嫌武松無知識,林黛玉不健康。欣賞跟崇拜也是分得開的。欣賞是情感的操練,可以增加情感的廣度、深度,也可以增加高度。欣賞的對象或古或今,或中或外,影響行動或淺或深,但是那影響總是間接的,直接的影響是在情感上。有些行動固然可以直接影響情感,但是欣賞的機會似乎更容易得到些。要培養情感,欣賞的機會越多越好;就文學而論,古今中外越多能欣賞越好。這其間古文和外國文學都有一道難關,語言文字。外國文學可用語體翻譯,古文學的難關該也不難打通的。
我們得承認古文確是“死文字”,死語言,跟現在的語體或白話不是一種語言。這樣看,打通這一關也可以用語體翻譯。這辦法早就有人用過,現代也還有人用著。記得清末有一部《古文析義》,每篇古文后邊有一篇白話的解釋,其實就是逐句的翻譯。那些翻譯夠清楚的,雖然羅唆些。但是那只是一部不登大雅之堂的啟蒙書,不曾引起人們注意。“五四”運動以后,整理國故引起了古書今譯。
顧頡剛先生的《盤庚篇今譯》(見《古史辨》),最先引起我們的注意。他是要打破古書奧妙的氣氛,所以將《尚書》里詰屈聱牙的這《盤庚》三篇用語體譯出來,讓大家看出那“鬼治主義”的把戲。他的翻譯很謹嚴,也夠確切;最難得的,又是三篇簡潔明暢的白話散文,獨立起來看,也有意思。近來郭沫若先生在《由周代農事詩論到周代社會》一文(見《青銅時代》)里翻譯了《詩經》的十篇詩,風雅頌都有。他是用來論周代社會的,譯文可也都是明暢的素樸的白話散文詩。此外還有將《詩經》、《楚辭》和《論語》作為文學來今譯的,都是有意義的嘗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