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一種甜作文 推薦度:
- 清明散文 推薦度:
- 感恩遇見的唯美句子 推薦度:
- 感恩遇見的句子 推薦度:
- 童年趣事散文 推薦度:
- 相關(guān)推薦
有一種遇見散文
三天內(nèi),集中起時(shí)間讀祝勇的《在故宮遇見蘇東坡》。作者通過(guò)故宮里的藏品來(lái)解讀蘇東坡。東坡在讀者面前,首先是書畫家,其次才是詩(shī)人。當(dāng)然也不會(huì)忽略他在其他方面的成就。這些藏品,有蘇東坡的,也有其他時(shí)代的其他作者的,都與東坡有著極為密切的聯(lián)系。通過(guò)這些藏品,作者深入地解讀東坡的生命價(jià)值和精神內(nèi)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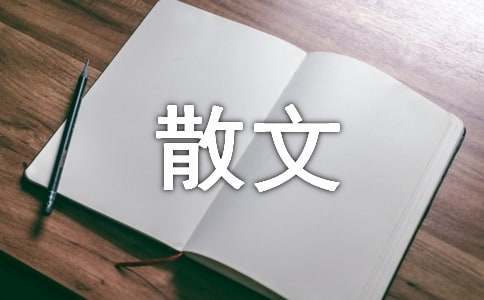
祝勇說(shuō),他是帶著敬意來(lái)寫這本書。而我,是帶著敬意來(lái)讀這本書的。對(duì)東坡的敬意,和對(duì)作者祝勇的敬意。祝勇沿著東坡的足跡跋涉,雖然歷經(jīng)千年,時(shí)時(shí)能感受到他脈搏的律動(dòng),作者滿懷的敬意流淌成文字,成為精神食糧,獻(xiàn)給那些喜愛(ài)東坡的讀者。
讀祝勇這一本,可說(shuō)是重讀。作者讀過(guò)林語(yǔ)堂先生的《蘇東坡傳》,文中有許多內(nèi)容都是依據(jù)林先生的那本,而我也讀過(guò)近兩遍的傳記,有些內(nèi)容在眼前時(shí),又都在腦海里。這一遍是重溫和加深的過(guò)程。
可又不僅僅是重讀。東坡的經(jīng)歷軼聞,經(jīng)了祝勇的妙筆,筆筆皆花。他強(qiáng)大的駕馭語(yǔ)言的能力,在我閱讀過(guò)的散文作家里,最令我欽佩仰止。更為重要的是,他身為故宮博物院的研究員,從藝術(shù)鑒賞的角度分析作品、透視作者更深刻,更透徹。在作品里對(duì)書畫作品的分析,實(shí)現(xiàn)古今中外聯(lián)結(jié),使這部書更具藝術(shù)價(jià)值。閱讀這本書,為我打開了更廣闊的視野,獲得了文學(xué)和藝術(shù)的雙重收獲,還有比這更大的收獲,是對(duì)蘇東坡的認(rèn)識(shí)和理解逐步加深。
邊讀著,邊感嘆著。
每一幅書畫作品都刻印著蘇東坡的心路歷程。《寒食貼》為人們所熟知,幾年前也一次次聽過(guò)蔣勛老師對(duì)于這幅作品的解讀。祝勇說(shuō),這首詞在東坡眾多的詩(shī)詞里不顯山露水,在他的書法作品里不可小覷。黃州,是東坡命運(yùn)的分水嶺,使東坡成功突圍。在黃州的第三個(gè)寒食節(jié),夜雨,宿醉,小屋如孤舟,窗外海棠花落于污泥之上,寒食思親,歸途遠(yuǎn)而無(wú)期,情景之所至讓東坡提筆寫下這篇不朽的`行書作品。讀詩(shī),會(huì)讀到他的低迷陰郁;看他的書法作品,會(huì)感覺(jué)到他的沉郁頓挫,有一種百折不回的精氣神。祝勇寫到“臥聞海棠花,泥污燕雪中”時(shí),“花”與“泥”二字,一氣呵成,有一種生命的流動(dòng),經(jīng)歷了痛苦的掙扎,走向?qū)掗熍c平靜。《寒食貼》使東坡的個(gè)性和精神揮灑到了極致。
在黃州,蘇軾完成了書法藝術(shù)中成就最高的作品。人們熟知的前后《赤壁賦》,都是寫于《寒食貼》之后,那時(shí),他的內(nèi)心已經(jīng)趨于平穩(wěn),從他穩(wěn)重的字體中可探知一二。字如其人,平實(shí)曠達(dá)與淡定悠然皆在其中。
書中佳詞麗句華章比比皆是,有如優(yōu)美動(dòng)聽的樂(lè)曲,宛轉(zhuǎn)悠揚(yáng)。祝勇豐富的詞匯,總會(huì)把人帶入一片清新的芳草地。舊詞經(jīng)了他的筆,華麗變身,有了新鮮的面孔,給人耳目全新之感。“風(fēng)月流麗”“一窗梅影”“白芷秋蘭”“雨晴云夢(mèng)”……諸如此類,磁石般吸引著我的閱讀,邊讀邊在本上摘抄下來(lái),牢記詞句引發(fā)的畫意詩(shī)情。
更喜歡他對(duì)東坡居士精神高度凝練的精華之句。“蘇軾與陶淵明,像兩片隔了無(wú)數(shù)個(gè)季節(jié)的葉子,隔著幾百年的風(fēng)雨卻脈絡(luò)相通,紋路相合”“生命就像樹枝上一枚已熟軟的杏子,剝開果皮,果肉流動(dòng)的潮流鮮活芳香,散發(fā)著陽(yáng)光的熱度”“蘇軾與黃州,是一個(gè)豐盈的生命與一大片土地的相遇,演繹出最完美的歷史傳奇”……讀來(lái)贊不絕口,只有真正懂得東坡的人,才會(huì)語(yǔ)出如此驚人之句。祝勇對(duì)東坡,有一種深深的認(rèn)同和默契。跨越時(shí)空,達(dá)成了一種神交,而且很深很深。
祝勇的文字總有一種代入感,讓那些已漸淡出又似曾相識(shí)的細(xì)節(jié)重返心頭,隨著人物的際遇感同身受。對(duì)友人,對(duì)弟兄,對(duì)妻妾,總是情深至極。因?yàn)閻?ài),所以愛(ài)。那一首首吟誦的詩(shī)詞無(wú)不是深情真情所寄。《蝶戀花》作于東坡在惠州的第二秋,彼時(shí)他與侍妾朝云家中閑坐,感于窗外瑟瑟蕭秋,煩憂在心,把酒吟詩(shī)而出。每每朝云撫琴而唱,最不能唱“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wú)芳草”,她從詞句中感到人生無(wú)常無(wú)奈,有一種生離死別之傷。唱及此句,便淚潸潸然。后一年,朝云染疫而去,自此蘇軾終身不再聽《蝶戀花》。讀到類似的情節(jié),總會(huì)為之感泣。蘇軾的一生,情感和政途總是波折,但他總是幸運(yùn)幸福的,總有愛(ài)他的女子心甘情愿地陪伴,想來(lái)還是他的人格閃閃發(fā)光。
在本書的結(jié)語(yǔ)一章,祝勇引用了木心先生的一句話來(lái)評(píng)價(jià)蘇東坡:他是僅次于上帝的人。這部書是蘇東坡的精神演變和發(fā)展的歷史,身為一介文人,也有著治國(guó)平天下的大抱負(fù)。他屢遭不順,總能為自己撫平傷痛,實(shí)現(xiàn)自我療救。在幾近于沒(méi)路中隱忍,為自己點(diǎn)亮一盞漁火,營(yíng)造出屬于自己的快意人生。人生不如意事總有八九,在閱讀蘇東坡時(shí),總會(huì)適時(shí)地與自己相遇,也會(huì)重塑一個(gè)自己,水窮云起,一片秋水長(zhǎng)天。
知道祝勇這個(gè)作家,只是在今年。在《散文》海外版上曾讀過(guò)他寫的《紙上李白》,洋洋灑灑、一瀉千里的氣勢(shì)真真是應(yīng)準(zhǔn)了李白的個(gè)性。更妙的還是祝勇老師的為文豐采,只那一篇,他的文化意味就已經(jīng)蔚為壯觀。后來(lái)在淘寶網(wǎng)搜書,才知道他早已經(jīng)卓著甚豐,從書名便知都是文化散文,洋洋大觀不讀也知。七八月份時(shí),有記錄片《蘇東坡》問(wèn)世,得知祝勇是總撰稿,便迫不及待地把六集一氣看完。精美的畫面,精彩的拍攝,還原了北宋時(shí)蘇東坡生活場(chǎng)景,解說(shuō)詞更是迷人,滿是詩(shī)情、才情,契合了東坡的文人氣質(zhì),那也正是祝勇為文格調(diào)。得知他將要出新書《在故宮遇見蘇東坡》,從預(yù)售時(shí)買下到書香拂面而來(lái),等得并不焦灼,如同等待一位摯友和故友,氣定神閑最適宜。
一直喜愛(ài)文化散文,余秋雨的散文應(yīng)該是我早期的閱讀,我讀遍了他的每一本書,帶著饑渴切切地讀,膜拜近乎癡狂。他滿足了我雙重需要,無(wú)知,無(wú)文采。那時(shí)候,為他寫了好幾篇讀書隨筆,都是興之所至,情之所極。后來(lái),這些書成了我閱讀的根基,站在這些書上,我看得更多一點(diǎn)點(diǎn),更寬一點(diǎn)點(diǎn)。
再讀文化散文,我已不是那時(shí)的我,讀的也不是余秋雨老師的書了。如果非要把祝勇和余老師分個(gè)伯仲的話,我更傾向于祝勇。他身為故宮博物院研究員的身份寫出的作品更專業(yè)更具體。對(duì)于祝勇老師,我似乎沒(méi)有發(fā)言權(quán),我只讀過(guò)他的這一本,也只是泛泛而讀。其他的書已在我的閱讀書目之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