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的散文 推薦度:
- 月亮的散文 推薦度:
- 雨夜的散文 推薦度:
- 清明散文 推薦度:
- 春天的散文 推薦度:
- 相關(guān)推薦
長調(diào)的追憶散文
一、長調(diào)的追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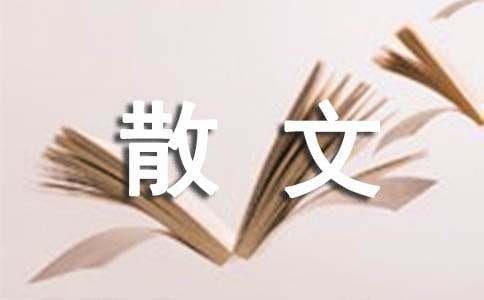
長調(diào),從草原孕育而生。
那些從肺腑里流曳而出的蒙古長調(diào),悠遠(yuǎn)地飄過來,飄過來,時而會華麗地抖動著,像鳥兒抖動翅膀飛入云端,融匯在草原的蟲鳴、鳥歌、牛羊歡叫的重唱中,里邊還攪拌了綠草與野花混合而成的氣息。
一個牧人,他為什么會顯得很孤獨呢?是因為離開了草原嗎?是因為到了一個陌生之所在嗎?他的孤獨是他所覺察不出的,所以我們也無從知道原由。
想起光布加甫,一位牧人,第一眼見到他的時候,他和一群民間藝人在一起,高高的個子,有些無措的雙臂垂在兩側(cè),在人群里,顯得那么孤獨。于是,也顯得那么惹眼。盡管他始終沉默著。
他頭戴著尖尖頂部的民族帽,身穿藍(lán)底金色印花的蒙古袍,站在一群神態(tài)各異、呈現(xiàn)動態(tài)的民間藝人中間,是惹眼的。他的表情,卻是凝重的,甚至處于一種靜止?fàn)顟B(tài),仿佛絲毫不受這個熱鬧的氛圍的影響。
他挺拔的個子,以及英俊的相貌,配合著他那身可能也是第一次穿的藍(lán)色盛裝,以及那種孤獨感,都讓他顯得卓爾不群。
他的古銅色面頰看上去有點疲憊。他來一趟縣城非常不易。他的家,就在草原上,從場部走還有80公里。
我們與一群民間藝人聊得忘記了時間當(dāng)然也忘記了他,他就不聲不響地坐在旁邊,不論我們聽歌、聽琴、歡笑,都不會有他的聲音出現(xiàn)。當(dāng)我們與民間藝人握手、合影、道別以后,才有人提醒我們,把他給漏掉了。
于是,帶著慌亂和歉意,我們請他跟我們一起去吃飯,這樣就可以從容地與他的交流。于是,在正午刺目的白光里,我們瞇縫著眼睛,忍耐著火辣辣的空氣烤灼,大步流星地往回趕,因為開飯時間早已過了。他就默默地跟著我們走向了飯桌。那天的飯可能正適合他的口味:風(fēng)干羊肉抓飯。饑腸轆轆之時,那些有些變涼的抓飯吃起來仍然挺香。我們謙讓著光布加甫,請他吃肉。不經(jīng)意間,卻見他已經(jīng)小刀在握,抓起骨頭,熟練地剔起肉來,儼然是在他自己家里一樣。然后他就做了一個“請”的手勢,讓我們吃肉。我們看到了一個寬厚淳樸的人,從他的緘默里顯露出身形。
只有在談起蒙古長調(diào)的時候,他的臉部表情才變得活躍了一些。
在寂寞的草原上,他唱長調(diào),常常可以唱到淚流滿面。
是的,面對草原的廣袤,人就像一粒塵埃一般渺小,無足輕重。于是,人太容易被草原所忽略。
每當(dāng)此刻到來,草原就藏著一個隱形的黑洞,任何東西都有可能在瞬間被吸走,無跡可尋。
人的孤獨感也是由此而來。
在空曠之處,為了擺脫被這個世界所離棄的孤獨與恐懼感,人必須要弄出一點聲音來,以顯示自己的存在,哪怕是為了娛樂自己。當(dāng)人的聲音與大自然的種種聲音交匯融合,當(dāng)人類被自己的歌聲所感動了的時候,他們以為,他們也感動了草原,感動了自然萬物。
而那些悠長又悠長仿佛曠遠(yuǎn)的時光的長調(diào),就是一望無際的草原,那些時而顫動的華麗音符,就是開放在草原上的美艷花朵。
長調(diào),就是這樣,帶人走進(jìn)了開滿爛漫野花的大草原,走進(jìn)了大草原的深處,然后,自己也變成了草原的一個景致。
那些長調(diào),聽著聽著,直教人生出一種渴望,渴望仰躺在幽深的草原上,淹沒在那些醉人的音符里……待到浸滿了草原的汁液,你就回到一片自己的棲息地,像馬兒一樣,悄悄地,在寂靜的黑夜里反芻、品啜,再度重溫那些天籟般的歌唱……當(dāng)你墜入夢境的時候,就為自己尋找到棲身家園后的恬淡與寧靜。
這些先祖代代相傳下來的東西,都是經(jīng)過了無數(shù)人的生命體驗而締結(jié)的智慧。先祖?zhèn)兙褪窃谶@些智慧里活過一生。這些藝術(shù)的結(jié)晶給了快樂更多快樂,也給了憂傷更多安撫,它引領(lǐng)人們暢游在彩色的歡娛的高空,得到飛起來一般的'通透淋漓的美好享受。
先祖?zhèn)冋J(rèn)為人就應(yīng)該這么活,所以就將這些東西當(dāng)做了無形的財富傳給了后人。傳承的工程是自覺自愿進(jìn)行的,一個民間藝人往往家里已是幾代傳人。我們接觸的民間藝人,就是從先祖那里接過了一代代傳下來的接力棒,口口相傳,全憑藝人耗費一生的精力去學(xué)習(xí)、去銘記,然后想方設(shè)法再傳給他們的下一代。
當(dāng)人類得以在代代相傳的智慧中一波波上升,才能夠離神性更近。
于是我們驚覺,現(xiàn)代文明讓我們逐漸偏離了那些草根的本真時,其實也使我們偏離了生命的本真。
循著長調(diào),溯流而上,我們找到了作為一個人來到這個世界的根究竟在哪里,也找到了生命花開花落的脈絡(luò)。我們觸摸到了從遠(yuǎn)古河流飄來的民族的記憶,也依稀體會得到那一脈同生的情感的溫度。
我恍然理解到,在蒙古人的生命中,既可以隨時領(lǐng)略《江格爾》的英雄主義氣概,也會任由激情萬丈的祝贊詞賁張血脈,更可以高歌一曲蒙古長調(diào)釋放那些情感思念……人類就是這樣運用了各種途徑,通過詩詞、歌唱、器樂、舞蹈,最終打通生命的邊邊角角,生命如同河水一般流動以至流暢,以至一瀉千里,就不會有陰翳遮蓋了陽光的映照,也不會有郁積阻滯了快樂的抵達(dá)。
接近精神的本源,其實就是如此簡單。對于一個人來說,漫漫人生,就像是望無邊際的草原,而那些先祖?zhèn)兞鱾飨聛淼拿耖g文化藝術(shù),就是草原上色彩繁復(fù)的花朵。
一曲長調(diào),就這樣,將一個悠遠(yuǎn)的博大的天地向我們展開來,當(dāng)我們漸漸地被引領(lǐng),被淹沒,被融化了的時候,就是長調(diào)留給我們的最美妙的印記。
二、聞馕則喜
聞“馕”則喜,是我對馕最露骨的表達(dá)。
馕,在生活于新疆的人們的眼里,總是帶著麥香氣息。聞之,口水涌流的幸福感就會從心里冒出來。
去年在庫車縣的一個火熱鄉(xiāng)村,路過馕鋪,正巧一只馕從馕坑里被勾出來,拋向半空中,馕和我打了個照面,金黃金黃的,上邊還有絲絲點點的紅花、洋蔥,美艷之極。而最不能忍受的是一股說不出的馕香,迅疾竄入我的嗅覺,我不禁深深吸了口氣,那種味道就又迅疾散布,以致邁不動腳步。
停下,看那個臉上油亮亮的打馕人。那個打馕人跪在馕坑邊兒上,正將一個柔軟的面餅在手上旋轉(zhuǎn)幾下,用刷子往一個碗里蘸了蘸,那碗里盛著用鹽水調(diào)配好了的細(xì)碎洋蔥與紅花絲,以及噴香的孜然調(diào)料。然后,放在一個大大的半圓形布包上,嘭的一聲,非常果決地拍到了馕坑內(nèi)壁上,馕就牢牢地粘在上邊。觀此過程的人,才能領(lǐng)會何以名為“打馕”。
如此這般,馕一個個地粘上去,圍了一圈,我探頭望下去,仿佛花朵開放在四周。馕坑底部,是燒得紅紅的火炭,既溫柔,又火熱,像是早就等在那里的懷抱。
恰到火候的熱度,慢慢地將白色的面餅烤到色香噴薄。大約十分鐘后,飄著洋蔥和孜然香味的馕,就一個個地被拋出馕坑,擺在最顯眼的位置,等待著悅己之人。
馕在新疆,就是因一些微小的區(qū)別,而有了各個地方的本地特色。
到了和田,馕也像庫車的那樣,很大,看上去不似庫車馕那么美艷,素樸的外表下,卻另有一番打動味蕾的美好。那美好全在吃到嘴里的一剎那間閃現(xiàn)。那是一種惟有在緩慢的火候里被緩慢地逼出的麥香,是惟有和田那緩慢悠長的時光才能夠烘焙出來的纏綿味道。和田馕的悠遠(yuǎn),需緩慢地品,才可知。一旦知,便如知己,無法忘懷。
在尉犁縣羅布人村寨,滿眼里盡是小巧玲瓏的馕,仿佛小點心,里邊放了羊油,酥香噴鼻,在燥熱的天氣里給人怡養(yǎng)和鎮(zhèn)定。這種馕,可以放置很久而不壞,適合與旅人為伴。
拜城的馕,長著大眾面孔,卻由于出自古絲綢之路龜茲國所在地,而有了別樣的美妙氣息。
難道是由于馕擁有千年光陰,才會被今人如此鐘愛么?“馕”源于波斯語,由此可以望見馕的源頭。古時稱馕為“胡餅”、“爐餅”。《突厥語詞典》還稱馕為“埃特買克”和“尤哈”。據(jù)記載,張騫鑿?fù)ㄎ饔蚝螅纬蔀轳勨彾.?dāng)?shù)慕z綢之路上不可或缺的美物,從西域流傳到中原,直至宋代,對中原的飲食文化產(chǎn)生很多影響。
而新疆的行者,每每遠(yuǎn)途,褡褳里總是裝滿了馕,沿著塔里木河、葉爾羌河抑或別的什么河走。餓了,停在樹下,將已經(jīng)久放而風(fēng)干的馕放進(jìn)河水里沾一沾,馕就吸飽了水,吃下去,腿上有了力氣,繼續(xù)走。從古時至今,都如此。
在新疆各地,走進(jìn)少數(shù)民族人家,幾乎無一例外,女主人首先端上來的待客食物就是馕,或用手撕開,或用刀切片,當(dāng)她精心地打開那個布包,攤開,悠悠麥香就連同一種情意,傳遞給做客的人。客人也坦然接受這份情意,或多或少地吃一點,以示謝意。
我對馕的牽念,隱在骨子里。而如此強(qiáng)烈的情感,還是從上大學(xué)顯現(xiàn)出來。我那時并不知道去北京上學(xué),遠(yuǎn)離馕的統(tǒng)領(lǐng)范圍,竟會有失魂落魄之感。四年,我的心一直在遠(yuǎn)方,在故鄉(xiāng),在馕的身上,須臾未曾離開。
十多年前,胃病嚴(yán)重,醫(yī)生的警告令人心驚。無意間發(fā)現(xiàn),一旦胃疼,吃點馕,就會緩解。于是暗喜,胃有不適就吃馕,以至于最后一日不可無馕。狂喜的是,不知不覺間,胃病漸漸痊愈。一位養(yǎng)生學(xué)家告訴我,原因在于馕在泥巴馕坑里烘烤的時候產(chǎn)生遠(yuǎn)紅外線,具有了怡養(yǎng)身體的功效。胃病好了,就是明證。
在新疆,若在街市,在公交車上,當(dāng)有人提著馕,總會成為最引人注目的一刻。那或焦黃或素淡的馕,氣息忽近忽遠(yuǎn)地飄過來,令一種需要倏地被勾出來,上下奔突。如果馕實在誘人,就有人忍不住追問:在哪里買的?提著馕的人也欣然告知馕的出處。
以前自行車多的時候,每每看見男人們把買來的馕往后座上一夾,一溜煙地回家去,就會心一笑。
許多外地人來到新疆,也被馕之美味所俘獲,臨走,總會帶些馕。前兩年出差去威海,看望一位在那里工作的新疆朋友時,忽然想到路上帶的馕,還剩下兩個,于是提了給他,他竟驚喜歡呼。兩個馕,一定是緩解了他埋藏心底的對新疆的懷念,也緩解了他對馕的思念。
在新疆,無論什么民族,都喜歡吃馕,雖說喜好可能有差異。有的愛吃油馕,有的喜歡蔥花馕,還有的喜歡吃用牛奶和面的馕……幾乎所有種類的馕我都吃過,但最后我返璞歸真了,我吃純粹的樸素的馕,上邊沾著些許洋蔥孜然,就心滿意足。
聞“馕”則喜,其實包蘊(yùn)了多少情感因素啊。
唯有久居新疆的人,才會從每個地方的馕的細(xì)微差別里,真正體會到馕的綿長滋味。這種滋味,也在時光的堆積中,慢慢地化作了心底里最溫暖的感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