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關推薦
甌居海中散文
南宋德祐二年農歷四月初八,文天祥來到江心嶼的日子確鑿有據。初夏的溫州,氣候清爽,草木滋潤,正是最好的時節,但文天祥的心情卻壞到了極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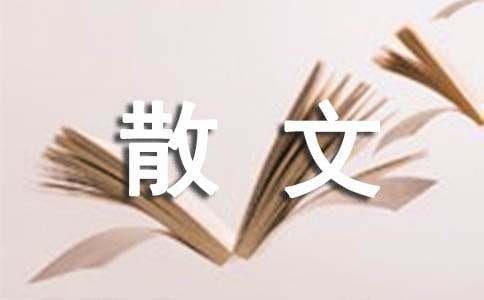
作為宰輔級的大員,出現在溫州的文天祥顯得突兀而狼狽。他是從元軍大營中逃出來的,滿身的血污說明了虎口余生的兇險。不過更令文天祥焦慮的還是國事之危。臨安政府已然投降,雖然各地還有義軍堅持抵抗,但在蒙古重兵碾壓之下,紛紛潰散,眼見得大宋即將全境淪陷,流亡君臣退無可退,文天祥憂心如煎。
文天祥在江心嶼共逗留了一個月,召集附近豪杰志士,日夜苦思恢復之策。然而最終也沒有理出頭緒,遂于當年五月離溫赴閩。
兩年后,文天祥再次被元軍俘獲。又次年,宋元兩軍崖山決戰,作為隨軍俘虜,他在元軍戰船上目睹了全軍覆沒之后,南宋最后一名皇帝、十四歲的趙昺被左丞相陸秀夫背負著,躍入海中。
比文天祥早幾個月,陸秀夫與張世杰也到過溫州。他們同樣在江心嶼上商討了復國大計。
他們還應該朝拜過同一樣器物。
江心嶼有座江心寺,以一副南宋狀元王十朋撰的“云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散,潮長長長長長長長長消”的長聯聞名。不過在王十朋與文天祥的時代,江心寺最為人所知的并不是這幅對聯,而是一把破舊的椅子。
確切說,那把木椅應該被尊稱為御座。因為當初北宋傾覆、金兵南下時,康王趙構的流亡政府曾經避難于此。后來趙構終于遇難呈祥,建國都于臨安,這把木椅也被視為見證否極泰來的圣物被鄭重珍藏。
可以想象文天祥陸秀夫第一眼見到那把落滿塵埃的所謂御座時的激動與希冀。然而當他們黯然離開時,都只剩下了滿腹的委屈與絕望。
江心嶼以東西雙塔為最著名的景觀,而這兩座唐宋古塔,一千多年來,除了宗教意義之外,也起著甌江上的航標功能——
然而天底下已經沒有任何一座航標能將文天祥的帝國之舟導出迷航。
云散潮消。一個殘破的王朝終于被漩渦卷入了海底。而在這個王朝誕生與覆滅的軌跡圖上,卻重疊出現了一座小小的島嶼:
文、陸、張三人,被后人并稱為“宋末三杰”;如果再聯想到一百多年前開國的高宗趙構,對于南宋,江心嶼,抑或整個溫州,意義顯得尤為深長。
正如此處方言的難懂,雖然同處一省,溫州一直給我一種神秘感。
我的家鄉金華,屬于浙江正中;但即便以浙中的角度,對于浙東南的溫州也有著相當深的隔閡。起碼在地理上如此:浙南多山地,人們常說蜀道難,浙南交通之難其實也不遑多讓。金溫鐵路建設難度之大、工期之長、耗費之巨,遠遠超出了同距離的其他線路。僅舉幾個數據,便足以證明此路架設之艱辛:從金華到溫州,全長不過251公里,計有橋梁135座、隧道96個,二者合計五十余公里,足足占了總長的五分之一。
但溫州又是如此如雷貫耳。在中國人的印象中,每個溫州人的額頭似乎都貼著精明與富裕的標簽。從打火機到眼鏡,從眼鏡到皮鞋,直到如狼似虎的“炒煤團”、“炒房團”——溫州人雄厚的資金,一度還走出國門,在洋人的地盤攻城略地,將他們嚴防死守的房地產界攪得雞犬不寧。
后來我又得知,溫州還是著名的數學家之鄉,出了姜立夫、蘇步青、李銳夫、潘廷洸等一大批數學大師,尤其是以蘇步青為首的中國學派,與意大利學派、美國學派鼎足而立,屹立于世界頂端。另外,馳騁棋壇近一個世紀,被稱為“中國棋王”的謝俠遜,同樣也是溫州人。
我總感覺,溫州這片土地蘊藏著某種被文天祥與陸秀夫忽視的力量——起碼在某種性質上,數學、弈棋,乃至于經商,都與兵法一脈相通。
他們離開江心嶼的踉蹌背影令人唏噓。不過,德祐二年,也就是公元1276這個年份,也使我想起另一件看似無關的事件:
就在幾個月前,旅行家馬可·波羅進入中國,在元大都覲見了忽必烈。文天祥逃亡時,馬可·波羅正隨著元軍的南進,細細觀察著這個古老的國度。
馬可·波羅是意大利威尼斯人。順帶一提的是,溫州還是浙江最大的僑鄉,而意大利,是他們最集中的僑居地之一。
令我想起馬可·波羅的還有一種氣味,一種由魚蝦鹽鹵等混合而成的淡淡腥氣。抑或說,是海洋的味道。
或是南貨店,或是小吃館,甚至居民的衣服上,行走在溫州街頭,經常會聞到這樣的氣味。它提醒著每一個過客,這是一座濱臨海洋的城市。
還有隨處可見的榕樹。如果說海洋的氣味暗示了溫州的經度,那么這種多須而張揚的植物則標注了這座城市的緯度。而這個由海洋與榕樹共同標注的坐標,常常會令行走其間的異鄉人陷入迷惘,尤其是在榕樹的旁邊,他往往又會看到一株樟樹——江南最為常見的樹種——枝繁葉茂。
按照廣義的范疇:長江中下游流域以南,南嶺、武夷山脈以北,即今湘贛浙滬全境與鄂皖蘇長江以南地區,溫州應該屬于江南。
事實上,溫州也具備著許多江南的元素。
馬可·波羅是否來過溫州,史無記載。不過,假如他看到溫州,定然會萌生一份親切。因為如同他萬里之外的故鄉威尼斯,溫州也是一個河網縱橫的水鄉。
溫州郡城始建于公元323年,設計者是中國堪輿學的鼻祖郭璞。郭璞依照此處的自然地勢,仿北斗九星格局,在城內挖掘了象征二十八星宿的二十八口水井,同時開通河道溝渠,將全城水系激活,奠定了號稱“斗城”的風水格局。在此基礎上,后世規劃者逐步深化完善,直至將溫州建設成中國六大風水城市之首。
雖然隨著城市改造古城變化極大,但直到今天,我們還能在溫州市區一一找到郭璞開鑿的二十八宿井以及形如北斗的的七座小山。當然,其中最為人所知的,還是塘河。
所謂塘河,指堤岸壘成的河流。塘河的稱呼多出現在東部沿海,用于抵御洪澇災害及潮汐。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溫瑞塘河。對于溫州,溫瑞塘河相當于母親河,水系總長度達一千一百多公里,而主干道,即溫州與瑞安之間,卻只有三十多個公里。兩個數字懸殊之大,足以說明溫瑞塘河分支之多、河網之密。溫州的老輩人至今還常常提起,數十年前的街路上還都是河,稍微去遠一點就得乘船。
溫瑞塘河的主干道,至遲在北宋時期便已經成為游覽勝地,沿塘河遍植蓮藕,號稱“八十里荷塘”。雖然早已過了采蓮季節,但乘船游河仍是一大快事。不過,雖然也有石橋宗祠,也有柑橘老樟、小村舊宅,也有釣客浣女、土狗肥雞,也是滿目的潮濕與蔥郁,但我總感覺到這片水土與傳統印象中的江南有很大的區別。
船行水上,我總想起,眼前漣漪淺淺的幽綠航道,最初是一條海峽;小槳撥開的,原本是苦澀的咸水。
當然,也可以更細化地將溫州的文化歸屬于甌越。
甌,一個詞義難以確定的古老漢字。可以根據偏旁理解為一個瓦罐之類的陶器,或飲酒,或盛飯;可以理解為一條江(甌江);可以理解為傳說中的一把利劍(歐冶子);還可以理解為一種鳥(海鷗)。
學界對“甌”至今莫衷一是的解釋,暴露了主流文化對這塊區域自古而來的疏遠與陌生。從《史記》《漢書》的東甌國開始,歷代史籍有關這座城市的記載簡之又簡,直到清代的顧祖禹,著《讀史方輿紀要》時,仍將甌江這條浙江省僅次于錢塘江的第二大河流一筆帶過,反而不厭其煩地去描繪短得太多的浦陽江與苕溪。
還有雁蕩山。這座當今堪與黃山平起平坐的名山,雖然早在南北朝便已經引起謝靈運的注意,但真正為人所知卻要等到北宋,并且在之后的幾百年間,長期荒蕪而蕭條,被稱為“雁山第一勝景”的三折瀑,甚至要到上世紀才被發現。
據說建城之初,郭璞曾經惋嘆過這座城市的命運,說此邑“此去一千年,氣數始旺”。
誠然,溫州距離中原太遠,隔阻的山嶺太多。但甌江與溫州的寂寞,果真只因為遙遠與交通不便嗎?游船上,我在資料中讀到了厚厚一本名人吟詠此地的詩詞,有王羲之,有謝靈運,有李白,有杜甫,有孟浩然,有韓愈……
這座城市、這條江的寂寞,難道還因為甌作為瓦器的粗俗、作為海鳥的野鄙,抑或,作為一把劍的不詳?
航船緩緩,經過一處古剎,據說那里原來聳立著一座名叫“白象”的古塔。
在溫州博物館,我見過塔內出土的文物。最多的是大大小小難以記數的神像,佛陀菩薩金剛力士,很多磚石上還刻滿了經咒——
寶塔鎮妖:這一方土地、這一脈水流,究竟隱藏著什么,值得滿天神佛這般如臨大敵,須得協力鎮壓?
溫州得名,在唐高宗時期,取冬無嚴寒夏無酷暑,氣候溫潤之意。在此之前,它一直被稱為永嘉。
作為一個永康人,永嘉二字具有特殊的意義。永嘉有個葉適,與我的南宋鄉賢陳亮同時代。二人都是大思想家,分別領銜“永嘉”與“永康”學派;在哲學史上,這兩派“永”字頭的學說氣質類似、觀點相近,屬于同一戰壕,因此也被合稱為“南宋浙東學派”。永嘉與永康都強調事功,提倡功利之學,反對虛談性命,一度曾與陸九淵的心學、朱熹的理學鼎足而立;但畢竟處于強調道德忽視利益的文化大傳統下,浙東學派缺少足夠的發展根基,很快在宋元之際走向沒落。
葉適與陳亮的思想,被很多人理解為替強權與欲望辯護,從而被認為是一種離經叛道的兇險學說,朱熹便將其視為心頭大患,連連哀嘆:“浙人家家談王霸,不說孔孟,可畏!可畏!”隨著朱子一步步走向神壇,作為他的對立面,永康與永嘉也成了不祥的名詞,被想象成一只裝滿了洪水猛獸的潘多拉魔盒,有意無意加以冷遇,甚至禁錮。
溫州在北宋時已經成為當時的港口重鎮,被朝廷辟為對外貿易口岸;宋室南遷后,溫州的海上貿易尤其發達,是全國四大海港之一(關于陳亮,至今有一謎團難解。他本是窮困潦倒之人,連安葬父母的錢都沒有,妻子熬不住苦,也搬回了娘家;中年之后卻突然暴富,大荒之年還修建莊園別墅。據他自己說是教授小孩子讀書,也就是辦學所得,但這寒酸的活計明顯只是個幌子。于是關于他的發家,有了種種猜測,如包攬訴訟、如敲詐勒索,但最多人認為,還是經商。證據是往來書信中,陳亮經常提到前往溫州會友,而他人際交往的禮品中,也常常見到內地不常有的水產海貨);而親手將朱熹封為圣人的朱元璋,即位后卻嚴令,舉國上下,片板不許下海。
與其他沿海城市一樣,失去海水滋潤的溫州很快開始枯萎……
“此去一千年,氣數始旺”。朱元璋與郭璞,相聚大致就是一千年。難道這位堪輿大師,當初算錯了這座城市的命運?
其實,小到一座城市,大到一個王朝,歷史的走向原本存在多種可能性。
或是一千多年,或是將近一千年。作為概數,郭璞的預言,同樣可以應在文天祥的時代。
溫州還是被譽為百戲之祖的南戲的發源之地。很自然的猜測,看到文丞相愁眉不展,溫州人很可能會安排幾場戲,給他解解悶,舒緩一下情緒。
據鄭振鐸先生考證,溫州南戲很可能不是本土自生,原型在萬里之外的印度,通過商賈漂洋過海傳來。證據是兩者有著包括結構、角色、情節、類型等等,許多難以用巧合解釋的相似。
我列舉南戲,只是想借一葉以知秋,說明這樣一個事實:在文天祥的時代,通過溫州,南宋王朝已經可以接觸到很多來自域外的事物,甚至已經滲透到帝國的土壤中,成為國人的日常。而趙宋王朝,在建國三百多年之后,已然萎靡軟熟,靠自身不堪振興。當年陳寅恪剖析大唐的輝煌,曾有過這樣的評論:“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華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且不提南宋面臨的正是塞外的壓迫,在十三世紀的世界,僅將塞外與海外做一比較,究竟哪處更多“野蠻精悍之血”,便可得知,其實帝國之手已經觸碰到了一扇重生之門,只待輕輕一推,便有可能脫胎換骨。
還是說回南戲。關于南戲,有一則史料被反復提及:“南戲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際,謂之溫州雜劇。予見舊牒,其時有趙閎夫榜禁,頗述名目。”(《祝允明·猥談》)趙閎夫是宋光宗趙惇的同宗堂兄弟,他發榜文禁止南戲演出,很大程度上代表著官方態度;元人劉塤則云:“永嘉戲曲出,潑少年化之,而后淫哇盛,正音歇。”亦可知文人對其的排斥。
的確,在官方或者精英階層看來,兩種文明最初結合產生的果實是丑陋粗俗的。但不屑一顧的同時,也就無法感受到其中蘊涵的無限活力。盡管在中國歷史上,南宋是一個對商業、對大海最為寬容的王朝,但它對大海的經營,更多還是一種消極的放任,尚未能以一種謙卑的姿態去主動尋求自己需要的東西。
覆滅注定到來。一扇能夠重新書寫歷史的大門就這樣與南宋王朝擦肩而過。我們無法苛求任何一個人目光短淺,就像無法拔著自己的頭發離開地球,誰也不能超越他所身處的時代。
江心嶼上的雙塔,即使能打出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航海燈語,落在文天祥陸秀夫眼里,也不過是秋風中瑟瑟發抖的螢火蟲。
俱往矣。我們登嶼的年代,溫州已然真正興旺。在嶼上眺望對岸,高樓劍聳,車人如龍,隱然有了幾分國際都會的氣質。
甌江東去。凝視濁流滾滾入海,忽然又想起那個既代表這條江,也代表這塊土地的“甌”字。“甌”的由來,是因為溫州北、西、南三面都有山嶺隔阻,唯一的出口只是東邊的大海,形如一個“匚”字,人類耕種于中(“乂”)而得主形。
忽然想到,我們國家的地形,其實也很像一個大大的“匚”字:大漠、高山,與雨林,暗暗畫了一個圈,把黃土地上繁衍起來的黃皮膚人圈在了里面。
好在我們的東邊只擋著一重薄薄的瓦。太久的風化,早已令這重阻攔搖搖欲墜:只要推翻它們,我們就能奔向大海。
當揚帆起錨,回望這片大陸,我們或許會感慨地發現,其實過往的千萬年,我們一直生活在海洋的懷抱當中。
就如《山海經》對溫州的描述:
“甌居海中”。
【甌居海中散文】相關文章:
居有屋散文04-16
不可居無水05-15
不可居無水05-15
身在花海中04-13
海中小島05-18
歲月不居05-13
春游團山名居05-19
參觀鎮海中學04-25
上海中考作文11-09
身處實地心居星空06-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