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有多遠的散文
你喜歡說:不遠,一點都不遠。于是,我順著你手指的方向,一直走,一直走。彎道繞過去了,溝坎跨過去了,樹木花草都看得眼花繚亂了,還是看不到行走的制高點。不管我怎么行走,四圍都是高山,層層疊疊的,氤氳著神秘的宗教氣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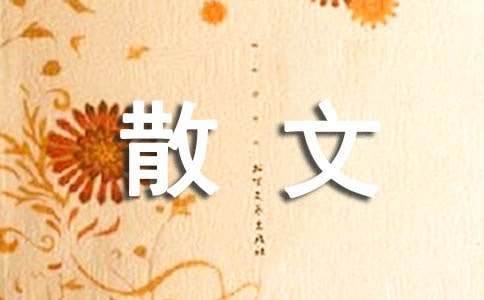
這山,不是自然之山,是人文意識構筑的文字山系。它橫跨五大洲,四大洋,穿越了莫桑比克海峽,竊取了古希臘神話的靈翼,攀上珠穆朗瑪的峰巔。我想,這峰巔,一定有著暗地生長的態勢。你前進一步,它長高一大步,甚或無數步。即使你每日不停地向上攀爬,也難以趕超它生長的高度。更多的人,仰望時喟然長嘆,靜坐時心生膽寒。只有那些執著的勇者,憑借超人的毅力,攀過一座座山頭,看高危的山體,孕育著何等超凡脫俗的雪之蓮。
百歲楊絳,一生都在讀書。讀過多少書,她自己也許都無法統計。楊家世代讀書,藏書頗豐。作為名門之后,楊絳打一落地便被書香濡染。父親《申報》評論一篇接一篇,母親料理一家大小衣食住用,得空總要翻閱古典文學,現代小說。這樣的讀書環境,給楊絳創造了良好的讀書氛圍。她不僅好讀書,還能讀好書。她在書山文海里游走,擷取智慧之珠,研磨成粉,敷之飲之,所以,自內而外,都浸淫著濃郁的書卷之氣。
錢鐘書,其父曾為清華大學教授。他嗜書如命,博學多能,圓融古今,貫通中西。《管錐編》一書,有人讀后驚嘆:“其內容之淵博,思路之開闊,聯想之活潑,想象之奇特,實屬人類罕見。一個人的大腦怎么可能記得古今中外如此浩瀚的內容?一個人的大腦怎么可能將廣袤復雜的中西文化如此揮灑自如地連接和打通?”還有外國記者曾說,來中國,有兩個愿望:一是看看萬里長城,二是見見錢鐘書。
楊絳與錢鐘書的結合,也是兩個大家族藏書智慧的融合。他們的涵養,是中國千年文化累積出的高峰,是中西文化交匯后壁立的巔峰。且不說《圍城》,就讀楊絳的《我們仨》,你也能讀出一代才女深厚的文化學養。即便是細碎的生活瑣事,你也能讀出流淌其中的文化氣韻。這樣的文字,不是一個腹中空空的人所能杜撰出來的。更難想象的是,它竟然出自一位92歲的高齡老人之手。隨手拈來的經典詩文,嵌入自己的敘述語言中,自然妥帖,看不到絲毫書呆子寫作時掉書袋的印痕。
百日壽辰,文匯報訪談,找來細讀,你會發現,楊絳先生,文思依然敏捷,出口成章,引經據典,毫無說教之枯燥。人類歷史上,能活至百歲者,大有人在,但是思維如此清晰,語言如此凝練,談論如此縱深,看待生死如此淡定,又有幾人呢?
沒有貼近生命的自始至終的閱讀,楊絳先生不會取得今日的成就。閱讀的先決條件是書,是有價值的好書。楊絳先生一生不缺少好書讀,有父母有師長,有丈夫有女兒,他們給楊絳提供了閱讀好書的廣闊空間。她也好讀書,能讀進去,能融會貫通。雖然成名比錢鐘書早,但是,為了丈夫,她依然退居其后,默默地操持家務,為錢鐘書創造良好的閱讀研究條件。甚至放棄公費留學它校的機會,陪錢鐘書在牛津完成學業。一個才女,她秉承著中國傳統婦女相夫教子的情結,無怨無悔地做灶下婢,弘揚了中國儒家文化的大愛與大德。她更多的作品,創作于70歲期頤之后。那時,錢鐘書的成就已經名揚海內海外。在他的盛名之下,楊絳依然默默地耕耘,不求聞達于諸侯,甘愿做錢鐘書的“老媽子”,陪其終老。
女兒錢瑗離去,相隔一年,錢鐘書也離她而去。她說,我們失散了。她說,我要整理鐘書的手稿。她說,我在抄寫《槐聚詩存》。她說,我已經走到人生邊上,等待“回家”。她還說,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還在尋覓歸途。她每天都在寫,不接受采訪,不參加售書儀式。她的靈魂是被厚重文明凈化的通靈寶玉,毫無世俗物欲的功利色彩,散發著纖塵不染的光芒。她不僅讀書寫書,更用蓮一般的德行,給我們從事文字工作的人立起一個標桿。我們得反思,要好好靜心反思:怎樣讀書,才能讀出這樣的一種人生大德;怎樣行走,才能走出這樣的一種人生境界?
其實,那些取得世界性文學成就的人,有幾人不是浸淫在文海書山的世界,暢游不已?那些世界性的文學巨著,哪一部不是作者豐厚學識外化的結晶?普魯斯特,福克納,伍爾夫,昆德拉,帕慕克,赫塔穆勒,村上春樹,等等,只要讀他們的作品,你便能讀到博識,讀到才氣,讀到洞察世相的睿智。伍爾夫的《論小說和小說家》,里面收集了她的十多篇論文,分別論述作者對奧斯丁,愛略特,康拉德,哈代,勞倫斯,福斯特等人作品的看法。閱讀文集,你可以看出作者的一些文學論點,如時代變遷論,人物中心論,主觀真實論,突破傳統框子論等,以及她的批評方式,如印象式,透視式,開放式等。沒有大量的閱讀,伍爾夫如何能寫出這樣透辟的文學評論,如何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高瞻遠矚,提出建設性的'批評意見。
伍爾夫的父親,萊斯利·斯蒂芬爵士是維多利亞時代出身于劍橋的一位著名的文學評論家、學者和傳記家。她身邊有一個知識精英的沙龍,就是著名的布盧姆斯伯里團體。其核心成員有:作家倫納德·伍爾夫(弗吉尼亞的丈夫),藝術批評家克萊夫·貝爾(范妮莎的丈夫),傳記作家利頓·斯特雷奇,文學批評家德斯蒙德·麥卡錫,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畫家鄧肯·格蘭特,藝術批評家羅杰·弗萊,作家福斯特。除此之外,哲學家羅素、詩人T.S.艾略特、小說家亨利·詹姆斯和奧爾都斯·赫胥黎也與布盧姆斯伯里團體過從甚密。這些“歐洲的金腦”多半是劍橋大學的優秀學子。弗吉尼亞·伍爾夫與這樣一批知識精英切磋文學和藝術,她不僅獲取了友誼、智慧和信心,還灌輸到自由平等的精神。她的文學創作由此別開生面,更加注重精神的含量。
伍爾夫的成就是精英文化濡染的結果。如果沒有身邊這些精英人才,沒有可供她閱讀的大英博物館,伍爾夫的才學會不會大打折扣呢?每次閱讀長篇巨著,我都會驚嘆:他們怎么會如此熟稔某種文化,而且不只是一種文化。閱讀《我的名字叫紅》,我驚嘆帕慕克對世界一流繪畫的精通。閱讀《紅樓夢》,我驚嘆曹雪芹對廚藝的精通,對茶藝的癡迷,對中國古典詩詞的融會貫通。閱讀《穆斯林的葬禮》,我驚嘆霍達對穆斯林文化的精通,對中國玉石文化鉆研的高度。小說是塑造人的藝術,有什么樣的人,就會做什么樣的事。這大大小小的事情,無不浸潤著文化的因子。如果不懂,你就很難把人寫深寫透寫神奇,把社會寫廣寫博寫逼真。畢竟,文化都是人創造出來的,人離不開社會這個大群體。
這樣看來,我們大多數人的文字距離經典有多么遠啊!我沒有書香世家的生長環境,沒有識字的父親母親,沒有可供閱讀的好書氛圍。流線型的讀書生涯,只為考試。流線型的教書生涯,也只為學生取得好成績。好書離我如此遙遠,我甚至不知道哪些書是好書。我也在閱讀,但更多的閱讀是為了考試。這樣的閱讀,讀不了好書。后來,即使拿到好書,也不知好在哪里。這幾年,認識幾位閱讀好書的良師,愛琴海,寇揮,安黎,向島,他們一邊給我開書單子,一邊教我如何閱讀好書,一邊診斷我寫作中存在的問題。把寫作和讀書結合起來,我才懂得應該怎樣讀書,讀什么樣的書。應該怎樣寫文,寫什么樣的文字。我的認識到位了,但是,我的閱讀幾乎沒有積淀。曾經,沒有閱讀寫作的氛圍,沒有愛書如癡的朋友。今日,即使認識到位,拉下的巨大落差,又怎能用極為有限的時間來彌補?
現在,我盡心盡力閱讀,渴望自己的閱讀能達到量的積累,引發我寫作方面的質性飛躍。但是,不管我怎么閱讀,都感到難以言說的貧瘠。特別是閱讀楊絳先生文字之后,我真的很難下筆,很難順暢地表達內心的生命體驗。如果,寫出來的文字是垃圾,耽誤了他人的閱讀時間,這豈不是一種謀財害命的罪過?過去,寫文字只是一種發泄,一種消遣,等上升到文學的高度,忽然就覺得沉重。文學是個神圣的語詞,不是每個寫字的人都能頂戴的花冠。如果要走進去,須得勞盡心骨閱讀不可。否則,寫出來的文字輕飄飄的,只能讀出故事的波瀾起伏。等卸掉故事的框架,就虛空得如同天邊的流云,轉瞬間便會消散了蹤影。
當然,閱讀很重要,更重要的是用閱讀的知識鑒別社會,透析社會。這樣,你就得先走出去,走進社會的大熔爐,在火焰的炙烤中體驗生命的堅毅,觀察人心的復雜,辨別人性的真偽。閱讀《我們仨》,楊絳先生與中華民國一起成長的人生閱歷,是她獨有的。那個時代,國際間的學術交流,民族的風云變幻,百姓的流離失所、動蕩不安,楊絳先生盡收眼底。用文字表達一家人的遭遇,牽出了一個民族的發展史,寫盡了祖國經受的種種苦難,也寫出了一代人前仆后繼拯救國難的勇毅。
我是一名普通的教師。更多時候,我呆在學校,接觸最多的是學生。不管校園,還是學生,相對來說,是比較單純的,是純粹的一方凈土。按部就班的生活工作秩序,決定了視野的狹窄。如果寫校園,寫學生,也許還能寫得深刻一些。但是,學校也不是孤立的,也不是脫離社會大環境而存在的。真的要想寫深透,還是要把學校復原到社會大環境中寫,這樣,你才能抓住時代脈搏里跳動的校園,有著怎樣的時代氣息。可是,我又如何能走出校園,融入紛紜復雜的社會,洞察它深厚的內幕?
遠,太遠了!你要問我有多遠,我真的無法給你說清楚到底有多遠。不管閱讀,不管閱歷,都是那么遙遠。那么,我該保持怎樣平和的心態,來面對我目前寫字的狀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