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通道里的拉琴者散文
五月九日。銀川風很大,樹如彎弓。風中,樹葉像一只只夜晚的流浪貓嗚咽、悲鳴、凄切的哀鳴。有點凄殘。此時,牽掛上學的丫頭,便沒了晚上赴宴的興致。電話告知友人取消約會后,時間尚早,恰離鼓樓書店不遠,順便進去買了兩本想了很久的梁實秋《雅舍小品》出來,沿著西北方向入口進入鼓樓“工”字形過道,準備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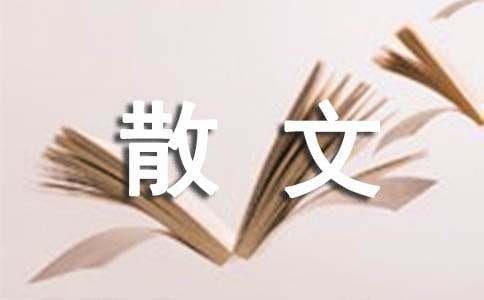
入口處,有三個常年在那討錢的人:一個斜跪著的老婦六十多歲,盯著自己乞討的碗;一個腿部殘疾爬著的年輕人,眼睛滴溜溜望著穿行的人;一個四十來歲的婦女,坐著閉目養神宛如小憩。這種習以為常的悲慘場景,把生命里那點脆弱、柔軟的同情心磨練的麻木而冷漠,已很難能讓匆匆的行走的腳步減慢下來。過了第一個拐彎處,地下通道里行人很少,顯得很暗,空落落的。一個五十出頭的男人,孤獨的拉著二胡。琴聲苦澀、凝滯、短促。我已走過,但無意的一瞥,卻讓我又轉身走到他的面前:那緊閉的雙眼,漠然淡定的面孔,那神情像極了老家荒蕪而從容的山頭,讓我突然產生了莫名的心動。這個拉胡琴的男人讓我想起了瞎子阿炳。“面對自身境遇的不咸不淡的心態,其中亦有一些處亂不驚的自我解嘲,一種骨頭很硬的幽默感。”
他也是!
我佇立良久,琴者如故,閉目自拉,旁若無人:一張蒼白的臉色卻很潔凈,一件藏藍的中山裝,陳舊而筆挺,褲子多皺褶,干凈而無污。屁股下木制的折疊小凳,也發出歲月打磨出溫潤的光亮。二胡如他,古舊而韻味十足。只是,二胡里的音樂由他而起,他生命的言語卻無法與人說清。整把二胡,從琴頭的內弦與外弦,再到琴筒、控制墊、和琴托,琴桿被他用左手的虎口日復一日的演奏摩擦出一份光亮,千斤之上和琴馬之下,與中間琴桿的本色形成巨大的反差,那被生命研磨的痕跡細膩、滄桑、潤澤。就是琴筒上的松香,也散發著人世間幽幽的風塵,散落到它的腿上讓人聯想。那把弓桿,在他的右手里或急促、或慢行、或停頓,弓毛在兩弦之間起起伏伏。有很多斷了的弓毛,雖再也發不出聲響,但依然隨著這份震動中顫抖。
但他不是瞎子阿炳。
無數的人有無數的命運。一樣的名間藝人,同樣的民樂,同樣同音承遞的旋律,同樣起伏連綿中的'律動美感,同樣道不完的苦,同樣流不完的淚,有的人只能在“獨滄然而泣下”,自嘆命運多桀隨波逐流,卻又一種人不甘自暴自棄,在困苦中沉思、反省和覺悟。如琴者,貧而不賤。用優雅稀釋凄苦,用音樂詮釋不幸,用詩意自我拯救苦難的靈魂。也如我故鄉的山戀——被世界教科文組織宣稱不適合人類居住的——西海固。被科學家們認為:寧夏不僅是一個得天獨厚的歷史地震遺跡博物館,而且是一部活的地震活斷層研究的教科書。沒人讀得懂那延綿千里貧窮的山巒,那如浪一般貧窮凝固的軀體里,那疼痛的身體里,對希望的信仰和崇拜虔誠。一份夢幻般的理想可以傳承幾代。
譬如讀書。
誰也想不到在這個貧甲天下的西海固,有著怎樣的讀書熱情和執著,有著怎樣的擺脫貧窮的決心和毅力,有著怎樣對命運不屈的頑強和堅韌。
我有個同學祖祖輩輩是農民,他的父親為了不讓同學成為和祖祖輩輩一樣的“睜眼瞎子”,在自家吃了上頓沒下頓的情況下,依然讓同學姊妹九個全部上完了高中,可惜一個都沒考上。08年,同學的大丫頭好不容易考上了,卻無力承擔每年一萬多元的學費。加上老家重男輕女的觀念,兩口子打算放棄孩子上學。沒想到八十二歲的老父親聽到后,拄著拐杖來到同學家里,二話沒說就給同學幾拐杖,說:“我把你個不醒事的!人活著,掙死不能窮死!把我棺材賣了,不夠的只要是我的兒女,都湊!只要娃娃有出息,我死了就是拉出去讓狗吃了也行。”
這就是我貧窮的西海固的父親,就這樣執著的一輩一輩地守望著一個夢。為夢而生,為夢而死的人。在十年九旱的自然環境里,滿眼的荒蕪中,心底卻擁有一個開滿無數鮮花的世界,一個充滿生機和希望的世界。這份對未來美好的憧憬,血液一樣融入了生生不息的生命,一代一代的在生命里遺傳著,經久不衰。
他們用思想開墾未來,用夢幻美化生命,對生命的完善如同宗教一樣虔誠。過去是,今天也是。西海固,便有了一目了然通透里說不清的深邃和內涵,一份貧窮里的雅致內涵。西海固的人也是這般,善思、多情。他們看不起跪著乞討的人,但他們會敬重每一個為生活所迫拉琴的人。
上帝過多的時間只給人美麗的追求,而不會給人圓夢。圓夢,是自己個人的事。臨別,我在琴者面前的盒子里放了十元錢,但這絕不是施舍,而是對他的如此活法從心底真真的尊重。
兩弦天地,一弓難敘平生;八方風雨,無言道明冷暖。但不管怎樣活著,跪,不能成為求生的理由,更不能成為生存的職業。
【地下通道里的拉琴者散文】相關文章:
圍墻里的狗散文11-10
櫥窗里的鐵皮玩偶散文11-12
網絡里的別樣愉悅散文05-02
融入秋的情境里散文11-19
映山紅里杜鵑啼散文11-12
情迷賽里木散文11-04
家游錦里溝散文11-03
在回憶里感謝你散文05-02
大灣里散文隨筆11-04
月光里的《海潮文韻》散文欣賞1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