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漢印象散文
當我寫下這個題目時,我忽然發現自己失語了。整整一個小時,我就這樣呆呆地盯著電腦,沒打一個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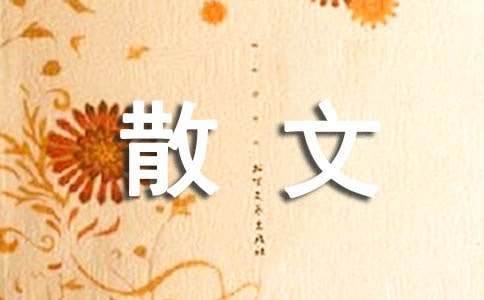
百度里沒有,手機里沒有,張允漢是誰?或者,誰是張允漢?
記憶開始時,是一點,接著,是幾條線,再接著,是一個輪廓,像素描。
那個下午,像一個逗號一樣楔入了句子。那個下午,空調壞了。那個下午……哦,記憶的導線終于找到了回憶的插頭,一切就亮了——
啊,是的,聚會,在十里堡的一個小街。有酒,有煙,還有服務員不斷的歉意。最后,還有一張消瘦的臉,一頭草書一般凌亂的長發,以及一道像射線一樣的目光。
語言終于在舌尖上蘇醒了,它泛濫,在泛濫中,我的耳朵打撈到了一個詞:書法家。
書法家,張允漢,真的嗎?
在酒精中漂,漂累了之后,是安子的建議,是一段樓梯后的另一段,是形而上的高度,三樓,離地面大約6米。
普洱很香,兌了墨汁后,更香。
你的手指在顫抖,那些宣紙上的舞蹈,那些被定格的姿勢,是你內心的單質嗎,有著晶格的形狀?
多少個夜晚被激情燃盡了,多少顆星漏進了你黎明的夢境?
修行,是一種積累,從一到十。
而修為,卻是一種減法,從十到一,無為,無不為。
所有的筆,都是虛妄的,當宣紙露出技術的胎記,當生存的堅硬腆起生活臃腫的腰身。
那一年,你才12歲,雪下得很大,雪地里有干枯的樹枝,和你凍紅了的手,雪地上還有字,橫豎撇捺,被風霜記錄。
那一年,在流俗的海報上,你多想為它插上徐渭的狷狂,但不能,一切是冰冷的,生活猶如一把刀,壓在脖頸。
時間在墨水中飄飛,似有紛揚的荻花飄過故鄉的小河,有些記憶只能化為墨痕,像老子離開那里,在函谷關留下五百言。
道可道,非常道。道可,道非,常道。如此之道,難道不是書之道嗎?
夜色壓彎了你的眉頭。鄭州,一個破舊的書案旁,一堆宣紙中,誰的愁思又驚飛了滿腔的困惑?
透支了體力后,再透支精神,喝光了所有的啤酒后,你就開始挪用頹廢?不,一切不應該是這樣的,一切應該是一輪圓月,沉靜地升在庭院的上空……
秋風哪里去了?還有閑月,抓著自己的頭發,你想把自己提起來。
放棄所有的欲望,像鐘表放棄發條,你醒來了,你躺在一灘思維的爛泥里,糾結你的,也不過是你自己。每個人都是自己的敵人。
倦鳥歸林,你忽然有了一種陶淵明式的散淡。像讀那涓涓細流,像讀那清風明月,你又疾筆在“忘我”的境界中飛奔了起來。開始是鐘、張,后來是二王,再后來就是米芾、王孟津了……
一切是那么的快,又是那么的慢,像重復著不能重復的消逝。
你開始相信自己了。你一開始相信自己,就覺得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了。美是有內涵的,它似乎對應著靈魂的暗物質,你這樣想的時候,墨還只流在你手上,等那些墨流到宣紙上后,一切都改變了。
我手寫我心,你真的能做到嗎?形而下的是技法,這精神的外延,而形而上的會是什么?人格著墨后的跡化嗎?
鳳凰涅槃,涅槃后的鳳凰,你目睹著自己一夜的衰老,形同在電梯里失重,突然墜回了原地。
心之追,手之摹,經年不舍的為何物?驀然回首,不也是一鳥一蟲,一塵一埃,等之平常物嗎?
見山是山,見水是水了。一切突然澄明起來。
涕零感懷,百轉千回,抵達夢境后會是什么?
沙漏里的一堆散亂沙,在時間的廢墟里,又有誰不是過客?但所有的真,都會留下,那些美好的終將是美好的,成為精神的里程碑。
·我的書畫朋友
“我的生活也從來沒有離開過朋友。如果說沒有這些朋友我還談什么我?我的人生和經歷可以說是與朋友們共同構成的。”
想起詩人芒克的這句話,就想起了我的生活,自然也就想起了我的一些朋友,在鄭州,搞書畫的人很多,而我認識的卻很少,算起來也只有寶松和豐倉二君了。
人與人相識是需要機緣的,機緣有時在乎于時機,有時在乎于緣分,而與二君結識,真可謂是一個在機,一個在緣。
認識豐倉君之前,就知道他的'名字,他的名字讓我感到了人們對土地血液般的依戀,以及對糧食豐收的渴求,凝重中裂殖著滄桑。后來,很偶然的機會,在一份雜志上看到了豐倉君的資料,介紹說獲過什么什么大獎之類的,這反倒使我看“輕”了他,我骨子里是一個徹頭徹尾叛逆者,對所謂的官方從來就不感興趣,覺得也不過“浮名爾爾”,等我真正地看到豐倉君的作品時,我才為之一振,有了拜訪他的想法。
想法是懸空的,落實到行動需要機會,也就是在那個想法產生后的第四天,由我主持的一家企業內刊要用一些書法的稿子,我馬上想到了豐倉君,于是,心中竊喜,“預謀”終于“得逞”。
黑夜給人的焦慮,在白天是難以緩解的,雖然它隱了形,化了妝,但它在人內心的投影是尖刻、撕裂的,在迷宮一般的鄭東新區,在18層的高度之上,在豐倉君的畫室,我能清晰地看到那附著在水泥鋼筋之上的人們內心渺小的痛,寫作是一場靈魂灰燼的揚棄,而繪畫則是一場熔煉——關于靈感、經驗以及視覺的提純。藝術的“單質”不在于實驗的結果,而在于整個熔煉的過程。
豐倉君寡言,但他的藝術卻呈現“多元”,從書到畫,雖然書畫同源,但卻風味別致,各有其特點。古人論之,書從劍,以氣養劍為至境,畫從心,心慧之處,景自現。若以此觀之,豐倉君行草可謂是飛劍如虹,行若恣意,而又不失規整,而其山水深悟用墨之度,自然之法,靈透中彰顯著個性,幾乎還耳于鳥鳴,還溪流于淙淙……
而與寶松君的相識,可能更多在于緣,緣這東西是飄渺的、形而上的,但它有內在的精神本源,即對寶松君作品的認知。
說實話,在看到一批帶有現代意識的女性畫時,我還猜想其作者一定是婉約清瘦的長發才子,等我見到寶松君時,我才真正感受到了藝術里常說的“意外”——寶松君敦厚壯實,粗線條體型,幾乎讓我覺得那些線條豐盈的女子,不是出自他的手筆。
也正是那日,飲酒多了幾許,酒酣之時寶松君突生感嘆:“中國的傳統快要喪失殆盡了!”一句再普通不過的話,卻讓我感受到了一個藝術家內在的良知和品質。
把西方繪畫的的形式和技法,如何融進國畫創作之中,一直是一個值得探索和思考的問題,所幸,寶松君已在這方面做了有益的嘗試,從原始彩陶、古代壁畫、石窟藝術、晉唐人物畫和民間圖案中吸取營養,并把這些元素運用變形、夸張的手法訴諸于自己的作品,不但強調了歷史傳承的人文性,而且,在美學意義上拓展了東方含蓄的審美意蘊。
書畫不分家,自古如是。水墨鑄就的意蘊,千百年就蕩起回腸于方寸之間,此次寶松和豐倉君的結合,可謂是珠聯璧合,相得益彰。一個以傳統書法功底勾勒皺擦,一個以學院派色彩構成橫涂豎抹,粗筆大墨,洋洋灑灑,一派大家氣象,使水墨靈透之風骨,在二君筆下一覽無遺,在這浮躁的、粗淺的浮華年代,顯得尤為珍貴。
如果說生活是人生的一種際遇,是與我們有關聯的一切的話,那么,其真正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呢?是那些落葉、長街和充滿愁思的秋夜,還是歡笑、悸動和淚水,我們又有誰能抵達它的核心?藝術又給我們的生活還原或再造了什么?
答案閃爍,如暗夜的星斗,卻又遙不可及……
【允漢印象散文】相關文章:
虞允文書生退敵01-09
說實話的高允01-09
王允計除董卓01-09
《全宋詞》陳允平07-05
虞允文統兵抗金04-22
虞允文書生退敵的故事11-09
關于王允計除董卓的故事10-24
《稱象》說課稿04-24
《稱象》習題設計04-29
課文《稱象》賞析04-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