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著心的獨自遠行散文
這是一次我所從未有過的遠行,一個人,還帶著一顆“心”。她曾經說:“當你到了草原上,盡情去感受它,你不是一個人在那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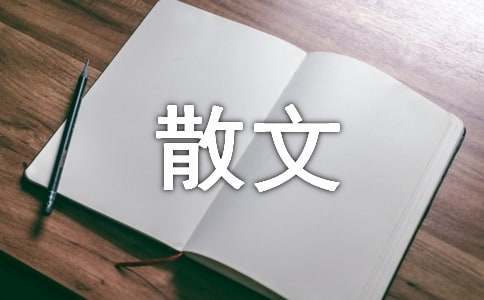
這是一個我叫它做《旅行筆記》的散文系列,是關于這次七天的遠行以及這顆一路伴隨著的“心”的部分記錄。在這七天的時間里,我從浙江寧波出發,去內蒙古的草原、沙漠還有成吉思汗陵走了一趟再回來。它所記錄的就這一路上的見聞所想之類。此外還有些別的東西,當然,所記錄的都是可記錄的。
我是個總喜歡沉醉于自己內心的人,就像這次的內蒙之行,看的少,想到的卻很多。這就使這一個“旅行筆記”不同于一般的觀光的文字,因為它里面的“風景名勝”很少,更像一次“心路旅程”。喜愛美景的朋友,或許要因此而失望了。前幾天有位朋友在看了我的“筆記”后留言:“有時候我們只是在觀光自己的心情!”我以為,這話確是我這個獨行者的真實寫照。所以,這個系列的文字,更多的是這一路的人事在我的心地留下的“痕跡”或者“波瀾”的描畫。
其實,這幾乎也是勢所必至的,隨著相機技術的不斷提高,復制景物已不再是文字語言的“分內之事”。而這一路上,我也一直在使用著這樣的記錄風景的“專事工具”,我自己知道,我的文字在這方面和它比起來要遜色許多。但它最后卻讓我失去了一些東西,這是我始料未及的。
關于這個系列的篇數的最后確定,說起來是很有些曲折的。開始寫時并沒有想著篇數的多少,只是順著時間順著一路走去的地點去寫。等到幾乎寫完的時候,我才知道一共是十五篇。本來在我的計劃里還有最后一篇記錄“歸途”的文字,而且已然寫下題目,但其時我在從草原回來的火車上只剩下“立錐之地”,無法可寫了。這樣一路擠而且急的回到了工作的地方,此后又開始“撲入”繁瑣的工作中去。再此后,雖多有時間,卻再沒有游行時的心境。這樣,到我開始來整理加工這些“速寫”稿時,這最后一篇也沒有使它從斷續的.念想變為文字。
等到整理加工的工作也幾乎完結,這個《旅行筆記》卻有了二十二篇的數量,有些東西,注定是要經過時間的發酵的。但是,這又似乎并非由于時間的發酵才使得它們更豐滿,最初的十六篇就像畫畫時的“速寫”,只是“用簡單線條把繪畫對象的主要特點迅速地畫出來”,而后還要不斷地添筆,使它更趨豐滿細膩。而且,照著我的“積習”,是一定要在這樣系列的正式“筆記”的前后各又加上一篇頭尾去的。這當然是受了先生的影響,于是,這個系列最后就有了這二十四篇的東西。
先前也有朋友問我,這一次的去草原,可有什么意外的收獲?我想了一想,回說是并沒有的。于我而言,能勉強算得上“收獲”的,也就只有這些的文字了,但可惜它們并不“意外”,而是我早先就打算要寫的。當然,意外的東西也是有,不過也不是“收獲”,卻是它的反面,是“失去”,我“意外”的失去許多先前的美好的期盼了。用我筆記里面的說法,就是“我親自一個個的將我先前的美好夢境拉到眼前,又用我的逼視的目光給擊碎了。”
不管是許久以來懷著的這個獨自遠行的夢,還是奔走遼闊草原的夢,或者那個徒步蒼茫大漠的夢,甚至于兒時就渴盼的得到一塊沙鏡的夢,都讓我這次一個個去靠近,一個個的去親手將它們打碎。雖則這打碎是一種“得到”式的,但所“得到”的跟早先的夢境卻全不同,于是我覺到的只是無聊,而此后還要獨自把玩這樣的“得到”,更讓無聊里添加了憤懣。
我后來想明白,有些夢想注定不能去接近,而只能讓它保留在它初發生的時空里,甚至不能久長的放在心里去逼視。這種情況適用于許多幼時的美夢,對待它們,就像對著一幅淡墨山水畫,它該有那一份的朦朧。這樣的夢想,你甚至不能專意去揣摩所謂的“意境”,我在《之二十一》里提到的幼時的小沙鏡,就是這樣的一個只能保留在偶爾記憶里的夢想。
但即便在想明白這些的現在,我也仍然忍不住要去走近那些先前夢想中的東西,甚至于要得到它們。
這是個奈何不得的矛盾。
所以,這一次的遠行,決不能算是我的“圓夢之旅”。那些真正能算做是我的夢想的東西,在目下這現實里是不能“圓”得了的。而這一個的系列文字里面的“基調”,就夾著這樣一種想要靠近又總是“打碎”、極盼望又每每失落的矛盾情緒。這是我這樣一個“孤獨者”遠行時的別樣心境的一部分。而這一次的旅行,既是一次“追夢之旅”,也同時是一趟“碎夢之旅”。
幸而,這一路上,還有一顆“心”在陪著。她給了我新的向前的希望,她也成了我的一個不會擊碎的夢。
最后需要聲明一下的是,在稿紙上的每篇原文的前面,我是都寫記了日期、天氣之類的“日記標志”的。也就是說,我開始是以“日記體”來寫這些“速寫”,但現在既然把它當成一個“散文系列”,這些也就不再抄來了。而況,這第二次“再創作”的東西,并沒有全按著原先的“速寫”,只順著時間日期的線索記流水賬,而是將這幾天的一些事件歸類編排,使它們順著我的“感悟”、順著我的“心跡”更協調的組成這一個的系列。
先前有一位熟識的朋友每每在看到我的一篇東西之后,總要來追問實際情況中的“真相”。我于是正告她:“你還要走出這一步,如果任一篇東西,你就馬上想到、甚至追問我的‘真相’,這不是對待‘文藝’的態度,更不是對待‘作者’的態度。‘作者’可以把自己的生活融入進作品,但作品并不完全就是‘作者’的生活。”
她聽了之后笑說:“看來,你已經不是那個只寫日記的小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