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草崗是我人生的胎盤散文隨筆
在江北圩區,村莊與村莊沒有明顯的區別,都無一例外地撒落在畫滿溝渠水網的平整田疇之間。有村莊的地方雖然都有樹,但沒有名貴的樹,大多是那種普通的苦楝、烏桕、泡桐、梧桐以及樺樹和梓樹。農戶家的房子無論是草屋還是瓦屋,都建得非常簡易,墻以土坯,或土坯、青磚混砌為主,全用青磚的不多,頂上蓋的要么是茅草,要么是灰色的大瓦片,蓋黑色小瓦的鳳毛麟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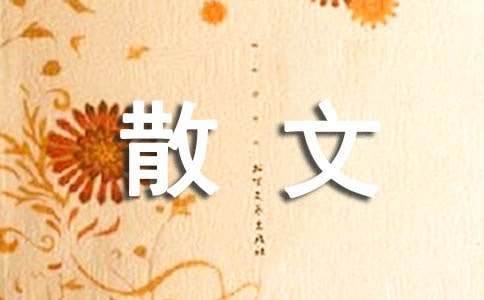
村莊有大有小,大的幾十戶人家,小的只有幾戶人家,無論大小村莊,均難見年代久遠的古屋。因為緊靠長江,常遭水患,遭遇一次大的水患,房子就要經歷一次劫難,或被洪水沖垮,或因水浸而倒塌,能夠歷水患而幸存的房子少之又少。
生活在圩區村莊的人總是有著與生俱來的憂患意識,他們被長江哺育,又害怕長江,不知道哪一天長江會發怒,會毫不留情地卷走他們辛辛苦苦置辦下的`微薄家業。過著面朝黃土面朝天的日子,他們辛苦勞作的剩余價值不多,即使是置辦下微薄的家業也極其不易,因此除了勤勞之外,他們養成了節儉的習慣。這種節儉,局外人很難想象。
40多年前,也就是上世紀60年代,我便出生在這樣的村莊里。我所在的村莊叫茅草崗,其實,那里只有茅草沒有崗,算得上崗的無非就是村莊里家家戶戶壘得高高的屋基,因為怕水淹,他們不得不將屋基盡量壘高,其實,壘得再高也只是一種自我安慰,長江的圩堤一破,屋基壘得再高也無濟于事。
這個叫茅草崗的村莊大約有30來戶人家,沿長江圩堤排成沒有規律的曲線。圩堤外面是依次是一條100米到50米寬窄不等的楊樹林帶,林帶外面是荒灘地,荒灘地的外面就是江灘了。每年長江的枯水季節,荒灘地可以種一季作物,但總是種得多收得少。這一季的作物大多成熟在汛期前后,汛期來得遲幾天,還有收成,若來得早幾天,就會顆粒無收,已經成熟八九分的作物眼看著被江水吞噬,總是叫人心痛得直掉淚。
因為是棉區,圩堤里95%以上的耕地種的都是棉花。圩堤外的荒灘地則大多種的是水稻,獲得的收成是村里人口糧的貼補,沒有了收成,便只好全靠回銷糧度日。吃過回銷糧的人或許都有很深的記憶,一是回銷糧不一定都是大米,有時候是老玉米或干地瓜片,即使是大米也是現在根本無人問津的陳化米;二是定量一般都不夠吃,只好以瓜菜代。
伴隨我整個童年的就是這個叫茅草崗的村莊。從記事起,恐懼和饑餓就一直如影隨形地糾纏著我。村民口口相傳的關于長江破圩的故事,總是縈繞在我的腦際,一到長江汛期,我無時無刻不擔心圩堤潰破,每個夜晚都會被洪水滔天的夢境驚醒。在漫漫黑夜里,我內心的憂患意識被恐懼的夢境催生,并一點點長大。
有兩種東西是我兒時的最愛,一是長江圩堤外面楊樹林里的茅草根,是鄰村桑園里的桑葚。因為回銷糧不夠吃,江外荒灘地偶爾的收成又被節儉的父母換成了磚瓦,人口本來就多的我們家總是過著吃不飽的日子,童年的我因此飽受饑餓的滋味。于是,楊樹林里的茅草地就成為我經常光顧的地方。茅草根一節一節的,就像縮微了的甘蔗。將拔出的茅草根放在嘴里嚼,有淡淡的香甜味,我經常是嚼著嚼著,就暫時忘記了饑餓。
桑樹結桑葚時不啻我的節日,在那段日子里,我幾乎每天泡在鄰村的桑園里,在我眼里,青的、紅的、紫的桑葚,是人世間最美的美食。盡管因此胃里有了充塞物,但必須為此付出代價,有時候,因為誤食了毛蟲爬過的桑葚,結果嘴巴種得比饅頭還要大,那種火燒火燎的滋味,不是親身經歷著不能體味。
茅草崗,這座最初哺育我生命的村莊,不僅決定了我童年的生活,而且對我的一生都產生了無法磨滅的影響。
【茅草崗是我人生的胎盤散文隨筆】相關文章:
人生橋梁散文隨筆11-03
我不懂的是我散文11-11
你是我眼中的美景,我是你曼妙的聲音散文11-10
我的夢一直都在散文隨筆11-03
足球是我的光作文03-29
我是你的詩人詩歌08-08
我的先祖是詩人詩歌06-23
大學勵志文章:人生的中軸是自己12-10
朋友,是人生最美麗的相遇散文12-14
吃虧是福,我是傻瑁的寓言故事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