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散文隨筆
翻開鄉村食譜,面是一個樸實、素淡而柔順的詞,安嵌在青黃更迭的鄉居生活的根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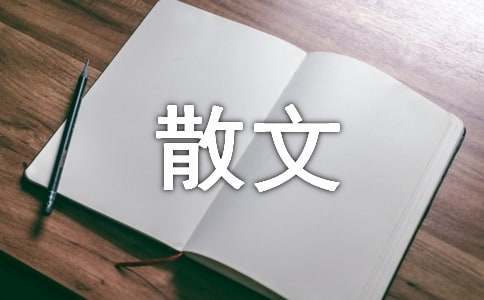
我童年時的面,既不是那種拜機器之力做成的粗細均勻規格統一的機絞面,也不是西北人愛吃的在空中揚成水波樣起伏的拉拉面。那是另一種百分之百的手工面,是在被搟面杖碾壓得薄薄的面皮上,用褐色菜刀犁出來的一種細長柔滑的面。在我的家鄉,它有一個泥土般質樸的名字———刀切面。
雖然饑餓的陰影在我的童年已躑躅遠去,上世紀70年代出生的人并沒有經歷過以挖草根啃樹皮來果腹的饑荒歲月。但在我兒時的印象中,那是一個稻糧等主食仍顯得十分拮據更談不上充裕和富足的時代,稀粥淡羹還時常出現在村人的瓷碗里,壓抑、限制著人們賁張的食欲。這時,不事喧嘩的麥子作為主糧的候補,從淺褐色的土壤中堅強地站立起來,并開始以各種姿態親近人們的胃。如果說大米是糧食的.父親,那么麥子則是當之無愧的母親,以一種帶土壤氣味的濃郁的芳香彌漫并滋養了整個鄉村。而面則是麥子母親的一種素面朝天的裝束(土黃色的面最接近鄉村年輕母親的膚色),一個柔順和美的姿態(纖細柔韌的面酷似農村勤勞女子結實而婀娜的身段),不矯不飾樸實淡定,把每一個愛吃面的農人的日子拉得綿綿長長,調得清淡滋潤。吃面,一般是在傍晚,這是否意味著面是對農人一天辛勤勞作的安撫和柔性延伸?農忙季節,村人在田地里忙了一天的活兒,當茂盛的夏秋陽光漸漸轉為沉靜的昏黃,他們便會三三兩兩或荷鋤或挑擔踏著野外赭色的田埂路回家。一到家,勤巧的主婦就卸下農具,洗洗還沾著泥巴的手,開始做一天中最后的一餐:刀切面了。裝一勺子頭茬面粉,倒進鐵鍋子里,邊添少許溶了點鹽的水,邊用雙手使勁地揉著。最后做出來的面條柔韌與否,關鍵在和面。父輩們的一句老話道出了和面的真經:“拳頭里面出細面。”其意是說只有雙手使勁地揉,反復不斷地揉,才能將水一點點地揉進面粉里,才能把面粉集聚起來,融成一塊雖然柔軟但結實,即使變形也不易折斷的面團——這就是面團的柔韌性,像堅強女性的柔中有剛的性格。我猜想,面團的這種令人贊嘆的個性,一定是來自那雙揉面團女人手中的力度和韌勁。
搟面,是把面團碾壓成面皮的過程。搟面的主婦在水缸上的砧板前,擺開一個略前傾的半站半蹲的姿勢,雙手緊緊壓住被卷在杖子上的面團中部,用力地將面團一點一點地往外碾壓開來,形成一張均勻的薄如紙狀的圓形面皮,微微泛出淡黃的光澤。第三道工序就是切面了。把面皮大約折疊成兩三重,刀鋒如一把犁將面皮劃成許多根一指甚至半指寬的窄窄的面條,然后小心地向兩邊抖開,收拾起來的話其實每一根都是很實在又柔和的一小把。
燒開一鍋水,再放入一些下面條的蔬菜(已事先熗熟)。青菜、洋芋,或者剛從屋前絲瓜架上采摘下來的一兩根絲瓜;還有可能是原本安靜地斜躺在背水一側塘堤上心形葉片下的青皮南瓜,都是拌面條的上佳菜肴。再燒開后,就將面條散散地抖落到鍋中——像是淳樸姑娘趕赴一個舞會前所化的一身更素淡的裝扮。稍等,湯又開,鍋子中間的面湯水燒得汩汩地往上冒的沸騰樣子,村人通常把它叫作“大滾”——柔韌滑爽的面條在沸水里上上下下翻騰,仿若無數個姑娘在空中歡快地飄舞。盛一碗,在面湯上灑些小蔥碎末或韭芽,則更見清香。
端上一碗刀切面,你可以自由地到鄰居家串門嘮家常,時不時地吸溜幾口碗里的面條;也可以一家人坐在自家低低的木門檻或屋檐下的小凳子上,用筷子緩緩地撩起碗中的面條,嘴巴從半空中斜向下湊近,一根或數根面條就“吱溜吱溜”吸了進去,把嘴一下子就填了個半滿,有一種吃出來的踏實感;興致來時,左手托碗右手握筷,晃悠到塘堤邊,蹲在半露水面的塘埠頭上。此時天色淡然,微涼的晚風拂蕩起池面舒緩的漣漪,一群小鯽魚在夕陽閃爍的金點中向岸邊偕游了過來。你下意識地收攏起悠遠的情思——邊欣賞小鯽魚浮出水面爭搶你故意投下的一小段面條,邊吸入一兩根面條津津有味地嚼著,或嘴唇就著碗沿喝上一兩口清湯。這場面,一如廣場上在風中搖晃的銀幕,飄蕩在鄉村向晚的風景里。
故鄉的面,童年的面,像一張黑白老照片或業已褪色的剪貼畫,張貼、招搖在鄉村悠久食文化的鏡框里,再現了村莊寧靜而舒緩、淡泊又從容的抒情生活;故鄉的面,童年的面,在很多從鄉村走向城市的游子內心深處,保留了多少恬淡、溫馨和持久的記憶。
【面散文隨筆】相關文章:
面行記散文隨筆09-09
熟莜面散文隨筆10-13
新疆的面散文隨筆10-17
見字如面散文隨筆08-23
西府百面鑼鼓散文隨筆07-27
母親的手搟面散文隨筆08-23
一碗牛肉面散文隨筆08-23
一面之緣散文隨筆09-03
好想吃一碗面散文隨筆09-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