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關(guān)推薦
今昔黎村見聞散文隨筆
第一次進(jìn)黎村工作是三年前的秋季。當(dāng)時是參加市里組織的“落實計劃生育工作隊”而在崖城的南山,赤草和抱古等管區(qū)的黎族村寨里待了近半年的時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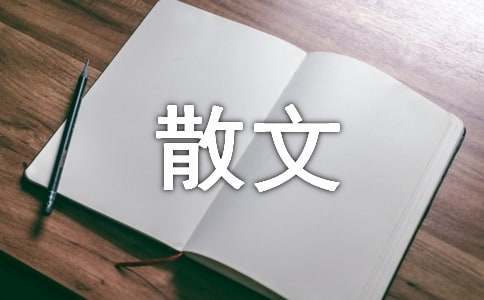
盡管早有思想準(zhǔn)備,但當(dāng)親眼看到黎族同胞的貧困狀況之后,還是讓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說是村子,看去只有十幾間歪斜低矮的茅草房毫無生氣雜亂無章地橫臥在小土坡上。草房頂上的茅草已成灰褐色,秋風(fēng)一吹,就有草屑紛紛揚揚地飄落下來,如果不是有幾只小狗跳出來狂吠,許多人都會認(rèn)為這樣的草房是不會有人居住的。我們彎腰走進(jìn)草房,大人不在家,只有幾個衣服襤褸光著腳丫的孩子瞪著大眼睛驚奇地望著我們。草房有四五米長,約兩米多寬,有不少洞孔的泥墻才一米來高。兩頭的門只有一塊門板。草房的一頭是煮飯和吃飯的地方。墻角里幾塊熏得烏黑的石頭就是灶臺。據(jù)說那只掛在泥墻上的舊簸箕,吃飯時拿下來擺在地上,就成了“飯桌”。草房的中段是臥室和倉庫。床是由十幾塊厚竹片拼成的,床上那塊舊毛毯已經(jīng)看不出原來的顏色了。另一側(cè)放著幾包用肥料袋裝著的稻谷和兩口袋木棉。算來恐怕是草房內(nèi)最值錢的東西了。
在村旁的樹底下,拴著幾條水牛,牛的糞溺四溢橫流,臭氣逼人,蚊蠅撲面;村民在混濁的河溝里洗衣物,飼鵝鴨,也從那里挑水吃。見到的村民,大都衣衫破舊。他們的眼神里只有求生的欲望,卻缺少那種擺脫貧困的要求,更沒有追求過好日子的信念。他們?nèi)匀槐慌f習(xí)俗、舊傳統(tǒng)和舊的生活生產(chǎn)方式所羈絆,像是被隔絕在已經(jīng)是瞬息萬變的世界之外……
半年后我們完成任務(wù)離開了黎村,可是除了在我的心里留下許多的遺憾之外,似乎還有許多難以釋懷的愧疚。我們還應(yīng)該為自己的黎族兄弟姐妹們再做些什么呢?
在本世紀(jì)的最后一年,我報名參加了市直屬機關(guān)組織的扶貧工作隊,到高峰鄉(xiāng)抱龍管區(qū)去繼續(xù)完成本世紀(jì)末的扶貧工作。
送我們下鄉(xiāng)的車子剛駛過高峰鄉(xiāng)駐地,那些在路旁牧牛的黎族老少認(rèn)出是扶貧工作隊的車子。都微笑著頻頻向我們招手致意,再往山里駛?cè)ィ赝揪涂煽吹揭粭l條新修的進(jìn)入黎村的公路和一幢幢新建的紅色的平頂房以及一行行已經(jīng)枝葉招展的芭蕉飛快地從車窗外掠過。這些都是扶貧工作隊留下的豐碩成果。
今天我們看到的'黎族村民,臉上那滿懷信心奮發(fā)向上的神情,已代替了昔日苦對赤貧而無可奈何的窘態(tài)。雖然大多數(shù)村民穿著衣服還是舊的、吃得也還并不太好,草房也還未全部拆除。但是,整個村子已沒有了當(dāng)年那種破敗凄涼和死氣沉沉的情景。就拿我們的扶貧點扎套村來說,全村共有十九戶,原來沒有一間磚瓦房,年人均收入不足五百元;去年扶貧工作隊幫助他們把年人均收入提高到了一千三百多元;蓋起了十一幢平頂房。計劃在二000年底,村民的年人均收入要提高到一千八百元,同時,爭取“消滅”全村的茅草房,讓家家戶戶都有一幢“風(fēng)雨不動安如山”的鋼筋水泥平頂房。然而,他們沒有滿足檳榔樹下剛蓋起的新房,也未滿足已達(dá)到脫貧邊緣的千多元收入。他們希望得到更多的種養(yǎng)項目和技術(shù)指導(dǎo);他們想讓更多的孩子上學(xué)讀書;他們要爭取承包更多的荒山。一位五十多歲的村民在自己新建好的房屋里緊緊地拉著工作隊員的手說:“是共產(chǎn)黨派來的工作隊幫我們蓋起了世世代代連做夢都不敢想的新房。”——這應(yīng)該算是代表了大多數(shù)黎族同胞的肺腑之言吧!今天,他們終于開始警醒:決不能讓貧窮和愚昧這些幽靈再回到黎村里來荼毒自己的子孫后代了!
如今的黎村,大多數(shù)都已修通“致富”路,從此結(jié)束了人們肩扛背馱的歷史;拉上了電燈,人們丟掉了火把告別了油燈;打了水井,村民不用再飲用那骯臟的渾河水了。通過加強精神文明方面的建設(shè),各村寨上學(xué)的女孩越來越多了,那些影響村民致富發(fā)展和身體健康的陳規(guī)陋習(xí)也正在被逐漸擯棄。一些先富起來的村民有了摩托車、三輪車;大多數(shù)的農(nóng)戶都有了比較現(xiàn)代的農(nóng)具;不少的家庭還買回了電視機……
黎家村寨的變化,雖然還不能說是翻天覆地的,但是,這變化確實是不同凡響的。我們相信,今后的變化一定會更加激動人心和令人難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