壓牛散文隨筆
我曾經目睹過壓牛的經過:一頭剛剛成年的灰色水牛,被一群人趕進空曠無人的大隊后,突然被關上大門,里面一片漆黑。漸漸地才敞開一道不大不小的門縫,門扇內的兩旁,各藏立著三條漢子,門外守著一條彪形大漢。然后,開始趕牛。起初,牛不肯出去,人們邊誘邊推,等到牛頭剛剛伸進門縫,身子還來不及出去時,六條漢子瞬間關緊大門,用身子死死頂住門扇。其余的人拼命地拉住水牛的尾巴,像河似的,不讓水牛跑掉,邊上觀看的孩子們,在大聲起哄加油。對牛來說,顯然拉牛尾巴無濟于事,只是過把玩的.癮而已。。關鍵是門外的大漢(全村的大力士,小名:監子,也是我們第二生產隊長,因輩份高,我們叫他“監子公”)迅速用肩膀扛住水牛的頭,把水牛前腳架空,無法使力。水牛被制服了,迅速將一根筷子粗的銅針及棕繩穿過牛的鼻孔,左孔進右孔出,鼻繩扎了一個結,再連接一條長繩子,延伸至牛的尾巴。水牛痛得“”直叫,禁不住流下了眼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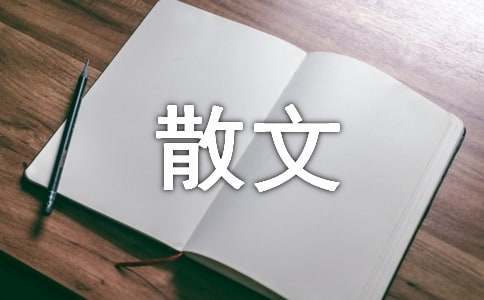
培訓師拉著繩子,把水牛牽下水田。在牛的脖子上安裝一根光滑的、圓弧的彎木,兩端各系著一條藤索,勾著牛尾后的鐵梨。牛伸著脖子步履維艱地拉著鐵犁。一開始,它很不情愿地掙脫著。時而,東奔西跑;時而,賴在田里不走。培訓師右手把著鐵犁,左手牽著牛鼻上的繩子、揮起鞭子“喔……撇……喔……撇...”(大概是左…右…左…右…的意思)的一邊吆喝,一邊敲打牛背。強制水牛接受訓練。經過兩三天反復的培訓,水牛才走上正軌。最終,勾出一塊塊,一畦畦,像光滑的早米糕,疊成的溝壑。
培訓師還在腰間綁著一個小竹簍,在犁田的同時,把翻土上的泥鰍、鱔魚、田螺、田蚌等逐一捕捉,放進小竹簍。成為餐桌上的佳肴。
從此,水牛承擔了生產隊全部的犁田活。
由于,犁田活含有技術,并非人人都會做,所獲得的工分,相比其它農活要高。所以,每戶家庭,至少都有一個人會使用水牛犁田,不愿失去高工分。
有時,我送飯到田間,乘著大人休暇時間,偷偷地把水牛牽下水田,掛上犁,“喔…撇…,喔…撇…”地吆喝著,手下的犁卻不聽使喚,總是東倒西歪,深一勾,淺一勾的打泥漿,翻不出完整泥塊。這絕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學到的技術。
后來,農村實行了分田到戶,水牛也就漸漸地消失了。犁田的任務,只能由人去代替。或父子、或夫妻組成搭檔,一人在前仰著身子倒退拉著,一人在后,腑著身子,雙手把著犁推著。勾著一道道、一丘丘的水田。人們才真正體會到耕牛的艱苦。
每年的暑假,高溫酷暑,父親總是帶上我外出打工賺錢。或上山劈草育林;或下田搶收早稻。雖然,不見鼻繩牽著、不見鞭子舞著,卻總覺得有一條條無形的繩索系著,掙脫不得。以致在后來養成了閑捺不住的習慣。
或許,有人從壓牛的事例中得到了啟發,把壓牛的過程演繹到教育子女的成長。常常揮著鞭子,“喔...撇..喔...撇...”地叫他們學這,學那。方式實在笨拙。或許,有人從耕牛的身上,得到啟示,沒日沒夜地辛勤勞作,甘心情愿地做“孺子牛”,又是何苦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