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i��)�����w��Ĺ��� ���]�ȣ�
- ���P(gu��n)���]
�P(gu��n)����������
����������һ��(g��)�����䌍(sh��)����ţ��׃��r(sh��)�ڵ����ѽ�(j��ng)�W(xu��)��(hu��)��Ԋ(sh��)��������С���ռ��������P(gu��n)�������Ĺ��£��gӭ�����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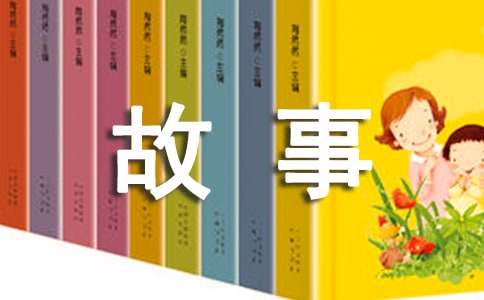
��������(��Ԫ650��676)�����Ӱ����ǡ������Ľܡ�֮��(������R��������������R��������e��)������Ԋ(sh��)�L(f��ng)�����£������x��ʹ���dz���һ�����ҡ����c�R�������˶�ԇ�D��׃��(d��ng)�r(sh��)����(zh��ng)��(g��u)�w�S�������̡���Ԋ(sh��)�L(f��ng)������27�q�r(sh��)����(xi��)�ġ������wԊ(sh��)�����~�x�е���ƪ����ĩ�����ġ������wԊ(sh��)���t����Ԋ(sh��)�еľ�Ʒ����Ԋ(sh��)���ַ���(du��)����Ԋ(sh��)���H��Ӱ푡��������ġ��Ͷ��ٸ�֮�����ݡ�һԊ(sh��)�����ǹ��J(r��n)����Ԋ(sh��)�OƷ�����С�����(n��i)��֪�����������������ɾ�����Ԋ(sh��)�����ܝB�Ž���(d��ng)���ĵ�ǧ�����䡣
�������������������ٻµ�Ԋ(sh��)��(sh��)�˼ҡ����游��ͨ������Ÿߵܣ�������˾��(h��)��(sh��)����������x�ȹ٣����(l��i)�˹پӼң���(zhu��n)�T(m��n)�����T(m��n)�v�W(xu��)����(sh��)���������С�Ԫ��(j��ng)���͡����f(shu��)�����鮔(d��ng)�r(sh��)��ʿ���Q(ch��ng)�����丸���ţ��v��̫����ʿ��Ӻ��˾������ֺ���϶��h��R���L(zh��ng)ʷ�ȹ٣������_(k��i)ʼ��(du��)���W(xu��)(���ޟ�)�����dȤ[1]�����������f�������^(gu��)�ˣ��ǂ�(g��)�������ͯ�������q���܌�(xi��)һ�ֺ�����;�Śq�r(sh��)�x���ע�ġ��h��(sh��)��������ָ����(sh��)�е��^(gu��)ʧ;ʮ�q�r(sh��)��һ��(g��)�µĕr(sh��)�g����ͨ�x����(j��ng)���o(w��)һ�c(di��n)�ϵK���B�������ѡ�ͬ������ͯ�����ė���J(r��n)������֪�R(sh��)�����쎧��(l��i)��(����Ȼ��ã��Է���Ӗ(x��n)��)��
����ʮ�Ěq�r(sh��)����������ͯ�����e�]���ڿ���������ǰé�����賯ɢ�ɵĹ�;ʮ���q���꣬����������ȥ��(d��ng)�渮������(du��)�����ǐ�(��i)��;ʮ�˚q���꣬���ڮ�(d��ng)�r(sh��)ʢ�ж��u������(g��)����֮�g�Ķ��u���ǟ��[�Ƿ��������_(k��i)��Ц��(xi��)��һƪ��ϭӢ���u��(��ӑӢ�����u��)���ǵû��ϴ�ŭ����������������������㵽�Ĵ�����ȥ���Σ����h(yu��n)�ν��h���ǽ�Ặ롱���õ�ɽ���`�����ұ������Ԋ(sh��)�����M(j��n)�����٣�����C(j��)������������I(y��)����ÿ��(xi��)һƪ���¶������@�@ٝ�p���e�ǡ����ݷ��ӏR���������J(r��n)�顰�ꂥ�^�ˣ�ϡ���錚�������(l��i)���ֱ����Þ�٣�����һ����Ĺ�ū���U(xi��n)Щ�Լ��G���������B�������HҲ�H�١��Ժ��������ڼң�һ������(sh��)����(d��ng)��27�q�r(sh��)(̓�q28�q)��ȥ��ֺ̽�����H�����ɺ���ˮ���@�¶��䡱��
����������һ���Ƕ̕��ģ�ֻ����27�q����ͬ�r(sh��)���Ǹ���׃���ġ��S����һ��������27�����������ġ����������鲢����һ��(g��)����80�q�����١�����һ��(g��)�������ͯ������˼�벻������ͬ�g�ˡ��������^(gu��)���W(xu��)�ij�����̫�࣬��˲����ױ�������ͽ��ܡ�����҂����������һ��(g��)����81�q���ˣ�ֻ���^(gu��)������ġ��ٶȡ��dz��˵���������������������(j��ng)�v�����^(gu��)��������һ�������ˡ��@����ȥ�^������һ������Ҫ��������öࡣ���ij����IJ��A�ͳ��̵������γ�һ��(g��)̫��ķ������ǧ�����(l��i)֪��������ʼ�K��ϧ���z�����Ї@���ѡ����^(gu��)���҂�?n��i)�����ޟ��Ƕ�ȥ��һ������һ���������X(ju��)����Ȼ�öࡢ�](m��i)��ʲô���z���ģ���?y��n)��κ�һ��(g��)�ޟ��˵�һ�����ǰ��Ռ�(du��)����(l��i)�f(shu��)������m���ޟ���·��(l��i)���ŵģ��vʷ����Щ�ɵ�֮�˾��Ǻ����p���ԡ�����������ʽ���x�_(k��i)�@��(g��)����ġ������̕���׃��һ���У��҂���������һ��(g��)�ޟ��˵ġ���������һ���S����ʵ�һ�l�ޟ��ĵ�·��
����������С���ǂ�(g��)��Т�ĵĺ��ӡ����H��(du��)���ܴȐ�(��i)������(j��ng)���̌�(d��o)���f(shu��)�������Ӳ�֪�t(y��)�������Ԟ鲻Т����������ӛ���^�����е�̎���L���t(y��)��ϣ���W(xu��)һ�ֺ��t(y��)��������(g��)Т�ӡ��ڹ�Ԫ661(��660)�꣬��(d��ng)����ʮһ�����q�r(sh��)���������@Ӡ������һ��(g��)�h(yu��n)�h(yu��n)���^(gu��)�������Ľ^�ÙC(j��)��(hu��)�����L(zh��ng)�������˲ܷ��ӡ��ܷ�����Ԫ���ֵ��棬�ԷQ(ch��ng)�Ǿ������ˡ���������o�ǘӏ��h(yu��n)̎�^���˵Ě�ɫ�������ҕ�˵����K����;߀�����A٢�ǘ����_(k��i)��ϴ�cһ�(l��i)�Ĵ����g(sh��)������(j��)����������ͽ���v���Լ��Ď��У�����(sh��)�H���ǡ��S�۰�ʮһ�y��(j��ng)����ֱϵ���ˡ�ԓ��(sh��)���Ϲ��ؼ������粮���o�S��;�S�������r(sh��)�ֽ�(j��ng)�^(gu��)��53��(g��)���˲ł����ܷ������С����@53��(g��)�����У����е���ʮ����(g��)���˱��o���������״��嶨��ԭ��(sh��)�¾�;߀�е���ʮ����(g��)�����A٢��
�����ܷ����mȻ�t(y��)�g(sh��)�߳�������С��֔(j��n)������������֪��������������Ҋ(ji��n)��r(sh��)�p�p��������һ�²��f(shu��)�������o(w��)��Ҳ���������ٴ������°ݣ��\(ch��ng)��������ͽ�ܡ��@�����������H��Ҳ�](m��i)֪�����ܷ��ӽ����������¾䡷�����S���؆�(w��n)�������y��(j��ng)����߀�С��������ס�����������T���ȵȣ�һ���W(xu��)��ʮ�傀(g��)�¡����֕r(sh��)����(du��)�����f(shu��)������(y��ng)֮�������S�������v��ᘾļ�ˇ�����S����ڽo�e��;��Ҫ�������ε��@ʾ�Լ�����(y��ng)��(d��ng)��¶ɫ��������ߡ����������Վ�Ӗ(x��n)���Լ����ĵ��W(xu��)�����꣬�K�ڡ������öÊW֮�ġ�������@��̫̓����(d��o)��Ԫ?d��)⡱���X(ju��)���Լ����w�е��۷xȫ���](m��i)���ˣ���(n��i)����������ˮa(ch��n)���˷ŗ�������������ɵ�Ը����
���������������������t(y��)������ޞ飬��������?y��n)����˃?n��i)ҕ�K���Ĺ��ܣ������_(k��i)ʼ�X(ju��)�á����g�}�p�������˲���������a(ch��n)���˅����x����w���Q(ch��ng)���х����g���������ľӱ���������������Еr(sh��)�������с�(l��i)�vһЩ����Ĺ��£��Еr(sh��)�Լ�Ҳ��(m��ng)���c����ͬ�Σ����l(f��)�����ˌ�(du��)ȥ���x�m����ԡ��ϼ���������������;��(d��ng)�r(sh��)�ĵ�ʿ��ϲ�g��ʳ��ʯ�衱���J(r��n)����˿��Ԏ����w����ҲŪ��������W�W�ġ���Ҳ֪���Լ���˼��ͬF(xi��n)��(sh��)��������ì�ܵġ�����20�q�r(sh��)��(xi��)�ġ���ɽ�R�����f(shu��)���Լ����W(xu��)�ɽ�(j��ng)�������ӛ�����·����L(zh��ng)���H�˾ͱ��Ҫȥ����ʳ���������֕�(hu��)���������ۣ��������Ժ�����ĸ������ڳ������(hu��)�С����������ǂ�(g��)���Ĉ�(ji��n)�����ˣ������Լ����ԵÕ�(hu��)�ɼҡ����¶��Q�ġ���ؑ�oһ�����������������g��ʧ����ֱ�����ص�����ֱ�������汧�㡭ȫ���ĵ�������?y��n)����ѽ?j��ng)�J(r��n)�R(sh��)�������������F�ߣ���Ҳ���������������Լ����������������F����ģ���������ظе��������Ǹ߲��ɜy(c��)�ġ�����20�q���ҵ����g�����ϲ��A���������Dz�ȡ�������������I(y��)�Ĵ�Õr(sh��)�C(j��)�����s���������g�Ęs�A���F���J(r��n)�����ǡ��ϲߡ������D���F���ǡ��²ߡ������һ��(g��)���������L(zh��ng)����(j��ng)�^(gu��)���S������Ŀ����ʹ�ĥ��������������һ����Ȼ����̫�y���£���һ��(g��)�L(f��ng)�A��ï�Ĵ����Ҫ�������g��ʧ����(ji��n)���ڵ�����(sh��)���ǘO���y�õġ�
�����������f(shu��)�Լ�������njW(xu��)���ܶY��żȻҲϲ�g�x��ҵĖ|�������(l��i)�x�˵��ҵĕ�(sh��)�Ÿе��c�Լ��������Ǻ��ˡ������ڡ����ݷ��ӏR�����Ќ�(du��)�ڿ��ӵķQ(ch��ng)ٝ�����ˌ�ζ�ģ���ʥ��֮�O(sh��)��Ҳ��������׃�����й����^��(y��ng)������أ���������������������Ⱥ����̫�ء�����������(j��ng)���f(shu��)����ʥ��������O(sh��)�̶��f(w��n)����ɡ�������վ�ڵ��ҵĽǶȰѿ��������������������e���δ��Ժ�ġ����塱������վ����ҵ͌ӵ����ϰѿ������³���Ȼ�����������˴��J(r��n)���@Щ�����塱�������^�кͰl(f��)�P(y��ng)���ӵIJ���˼��!
�����ܷ����������ژI(y��)�r(sh��)���Ƚo���v�������¾䡷���������(du��)��������Ҿ����������ԡ������f(w��n)��v�Ȯ�(d��ng)�r(sh��)һ�����X(ju��)�ú��y�Ė|�����������С�������߀�����^(gu��)һ��������ǧ�q�v�������Ƴ����˜�(zh��n)�����һǧ����õĚv��(sh��)[2]�����@Щ�|���ț](m��i)��ʹ����(du��)�����J(r��n)�R(sh��)�M(j��n)һ�����Ҳ�](m��i)��ʹ�����ޟ���ǰ���M(j��n)һ��������(du��)������һ���J(r��n)�R(sh��)�Ǐ��c�����෴�ķ���ȥ��(y��ng)�á���(j��ng)��֮�����õ��ģ������@һ��(g��)�J(r��n)�R(sh��)�ϵ��w�SҲ���������ܷ���һ�ӵā�(l��i)��һ��(g��)�����@���������澉��
�����������̿��@�С����ס���һ�Εr(sh��)�g���������������һ��(g��)��(m��ng)����(m��ng)Ҋ(ji��n)���Ӂ�(l��i)��(du��)���f(shu��)��������̫�O��������֮�������с�(l��i)��(f��)��ĥ���K������������ô���£���(xi��)���˶�ƪ��(du��)�����ס��Є�(chu��ng)Ҋ(ji��n)�l(f��)�]�����¡�������(j��ng)��(xi��)�^(gu��)��������װl(f��)�]���Լ�����Փ���ȶಿ���������(l��i)��ɢʧ�ˡ������@һ���J(r��n)�R(sh��)�ϵ��w�S���҂�?n��i)�Ȼ���ԏ����F(xi��n)���һЩ�����п���һ�c(di��n)���E��(l��i)�����ڡ����Բ�����Փ�������f(shu��)������(d��ng)��](m��i)����˼�]���](m��i)���ˌ�(du��)�κΖ|����ϲ�Õr(sh��)�����x̫�O�ľ�����ѽ�(j��ng)���h(yu��n)��;һ�п��Կ����Ė|������(l��i)��?x��n)Ƀx����(d��ng)����@Щ��Ҋ(ji��n)֮�ﶼ���øɸɃ���r(sh��)���Ǿ���̫�O����
�����x�^(gu��)�����ס������l(shu��)��֪����̫�O���Ƀx���Ƀx��������?��һ���˶�������@��(g��)�����l(f��)����·�������ߣ�ֱ����64��Ū�à��죬�ٰ����õ�������(w��)��ȥ�����˿����ء���ء��á���;�@Ҳ�����������f(shu��)�ġ���ɢ֮�t������;���ޟ���Ҫ������w�桱���ŗ�����͡��á������Ҫ���^(gu��)��(l��i)�����g�f(w��n)���лص�64�ԣ���?g��u)?4�Իص����Ƀx��̫�O��̫�O���ǡ��С������ǡ�һ����Ҳ���ǡ��㡱���@��(g��)�^(gu��)�����Ñ�(y��ng)�ˏ����S�����ġ���Ԓ���������t������t�ɣ�ֻҪ��������һǧ����ǰ�������@��(g��)20�q���ҵ����p�˾͌�(du��)���������e�nj�(du��)���ס�����˳������J(r��n)�R(sh��)���@��Ҫ���������S�����ˑM��Ī���ˡ�
�����������ޟ���·���ˑ�(y��ng)ԓ�Ǻܴ_�����ˣ����t(y��)��������������;�ֶ��dz�����ʥ�������H��ָ��(d��o)���߉�(m��ng)���c(di��n)���������ѽ�(j��ng)�������t�m�������������ص����Ƶĵز��������o(w��)�Ɇ�(w��n)�ؑ�(y��ng)ԓ��һ��(g��)���ҵ��ޟ����ˡ�Ȼ������ƫƫ�ڡ�һ���١����҂��@Ӡ֮���֡��ٶ��������҂�?c��)��@Ӡһ�أ�����ȫ��ȫ����������(l��i)��!
�������@�ز���ǰ�ɴΣ���ʹ�����ͻ�l(f��)�ԙC(j��)���](m��i)�б�����ӛ���(l��i)��
�����������������^���ѽ�(j��ng)ɢʧ���F(xi��n)�����µ�һ�������Ӱ������ѽ�(j��ng)�������絝�ʵ۸������g�̡������Ľܡ������r(sh��)����(j��)�����ռ�����һ�c(di��n)�ຆ(ji��n)��ƪ���϶��ɵĽY(ji��)��������҂��o(w��)��֪�����Q����ʼ�ԺΕr(sh��)��������(j��)�����Ӱ��������҂�����֪����20�q�r(sh��)߀�](m��i)�ЛQ������������ʽ�_(k��i)ʼ��������20�q�Ժ�27�q��ǰ��ij��(g��)�r(sh��)���������µ�ʮƪ�����У�������ƪ�����ġ����ݷ��ӏR�����⣬�����ƪȫ�Ǟ����(xi��)�ı���;�������Ӱ������е�����ƪ?ji��ng)t�ǡ�������(l��i)�ɵ�ӛ���͡���ȷ��x����
������չ��
���������w����������
������Ԫ���꣨675�꣩�ǰ����ֺ�������H��·�^(gu��)�ϲ��r(sh��)�����s�϶������������w�ɣ����(y��ng)���������w�����e�͡�ǰ����Ҋ(ji��n)��鐶������������⣬��Ո(q��ng)��Ҳ�������(hu��)��鐶����˴���ͣ��Ǟ������ҿ�ҫŮ���όW(xu��)ʿ�IJŌW(xu��)��Ů�����Ȝ�(zh��n)���һƪ���ģ���ϯ�g��(d��ng)�����d������(sh��)��(xi��)�o��ҿ������(hu��)�ϣ�鐶������ó����P������Ո(q��ng)�T�˞��@��ʢ��(hu��)�����֪���������⣬���Զ����o����(xi��)����������һ��(g��)��ʮ�ךq��������݅���������o�����^(gu��)���P����(d��ng)���]�P����(sh��)��鐶����ϴ��d�����¶����D(zhu��n)�뎤����ȥ��������(xi��)Щʲô�� (t��ng)�f(shu��)�����_(k��i)��(xi��)����ԥ�¹ʿ����鶼�¸������������f(shu��)�����^(gu��)��������Մ�������Ƿ����F���ؽӺ�]�����������Z(y��)���� (t��ng)��������ˮ���L(zh��ng)��һɫ�����������ò��@��������������ţ���(d��ng)�����࣡�����tӛ����������Ȼ��(du��)�Ͳ�����핿̶��ͣ��IJ����c(di��n)���M(m��n)�����@����
�����ȕ�(sh��)��ӛ��������Щ�䏈�����������_��(sh��)�鲻��֮��ƪ���������ϲ�鐶��������x�ļ�Ԓ����(sh��)���Ї�(gu��)�ČW(xu��)ʷ������(d��ng)�˵Ĺ��¡������f(shu��)���������ģ�������˼����ĥī��(sh��)�����t������������P����廣�Ԯ�P��ƪ������һ�֡�������Ҳ�f(shu��)��������ÿ�鱮힣���ĥī��(sh��)�������������P������һ�P��(sh��)֮�������Z�c(di��n)���r(sh��)���^֮���塣����(j��)�˿�֪�����������w�ϼ��d���xǧ����ƪ������̓����
��������������(xi��)�꡶�����w�������롣�Ђ�(g��)�Ѕ����µIJ��Ӿ��đѼ��ʣ��I�S����Ԋ(sh��)���dz��u�Լ��ġ�Ҋ(ji��n)���˲���,������߀��(d��ng)�����������w��һ�ֲ���ر�����(l��i),��Ҷ��ܳ��@,������(du��)�����������ġ�
�����Y(ji��)�������أ������@�ţ�����(w��n)�����������^(gu��)Ŀ�������������������(w��n)�@��Ԋ(sh��)ĩβ߀����Ԋ(sh��)���������һ�r(sh��)�Z(y��)����ֻҊ(ji��n)��������?y��)]ī����(xi��)��һ����Ԋ(sh��)��
�����������w�R��侣������Q�[�T���裻
������(hu��)�����w�����ƣ��麟ĺ����ɽ�ꣻ
�����e��̶Ӱ�����ƣ���Q���Ǝ��
�����w�е��ӽ���ڣ������L(zh��ng)����������
������(xi��)�T�����˽Է����o(w��)���Q(ch��ng)ٝ��������ֻ���������ˣ�һ�r(sh��)�@�������Ԓ��
�������������IJ��A�C���Լ��Č�(sh��)�����z���������g���������Ǵ����֮�L(f��ng)��
����������Ԋ(sh��)�跽��ijɾͣ�
����������Ԋ(sh��)��ֱ���^����ؑ�^�r(sh��)�ڳ�������ľ����L(f��ng)�У���ע���µĕr(sh��)����Ϣ���ȉ�������ֲ�ʧ������Խ�����w��(l��i)�v���̈́eԊ(sh��)����(sh��)���硢�ۜ���韣��硶�Ͷ��ٸ�֮�����ݡ���(xi��)�x�e֮�飬�ԡ�����(n��i)��֪������������������ο�㣬�⾳�_(k��i)韣�һ��ϧ�e���x�ĵͳ���Ϣ����(y��u)���o�k���[�s���ɣ��硶��ͤҹ���̈́e��������y���\�������w�����϶ˡ��ż��xͤ�ڣ���ɽ��ҹ���������L����һ�������Ľ�߅��ҹ�D����(hu��)�惞(y��u)�����ɣ�����������������l(f��)���������ı���֮�У��硶�eѦ�A��������Ԋ(sh��)���������㌑(xi��)ϧ�e֮�飬���Ǖr(sh��)�r(sh��)̎̎��l(f��)��(du��)�Լ������ı���֮�У�����֮ʹ�������F�������������̈́eԊ(sh��)�г��F(xi��n)�l�ʘO�ߣ���������(du��)ǰ;���\(y��n)��㯺���������ڱ��F(xi��n)���硶���Մe���L(zh��ng)ʷ���С�Ұɫ�\���F��ɽ�┿ĺ��������Ұ�\���ڝ������F�У��ຮ�����V���h(yu��n)̎��ɽ���ڳ���ĺ�\�о۔������أ�ɽ��Ұɫ�ں��Fĺ�����@���[�s���ɣ��Ɖ�(m��ng)�ƻá���˼Ԋ(sh��)�t��l(f��)��ǧ��֮���b�͵���У�˼����l(xi��ng)�������H�ѣ������Бѣ��硶�b�������tͨ�^(gu��)��(xi��)����l(f��)�����˼�l(xi��ng)֮�顣�@��ɽˮԊ(sh��)�Ȍ�(xi��)������(d��ng)���N����������Ԋ(sh��)�����ã���M(m��n)���C(j��)���硶���d����ͬ�r(sh��)�����茑(xi��)�ַ���Ԋ(sh��)���_(k��i)�صȷ��棬���M(j��n)�����µćLԇ����ȡ���@����ˇ�g(sh��)Ч�����h(yu��n)��ɽˮԊ(sh��)���H���չ�F(xi��n)�����U(xi��n)����������;���L(f��ng)�⣬������Aע�����e֮������@������������N(y��n)���
�������Ĺ��¡����P(gu��n)���£�
����?ji��ng)?chu��ng)���������w����10-13
����������07-03
�c������Մ08-27
������Ԋ(sh��)��04-12
���������wԊ(sh��)02-26
�����������w��12-07
